蒋云飞
【摘要】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关键词】 破窗理论;破窗效应;环境犯罪;场域控制;防控策略
一、破窗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一)破窗理论的历史沿革
为验证“外在环境与不良行为”的关联性,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69年做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实验:他将两辆完全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富人社区和穷人社区,然后摘掉停放在富人社区汽车的车牌并打开顶棚,结果这辆汽车很快被人破坏,车内值钱的部件被盗走,3天之后,汽车完全变成一堆废铁,而停放在穷人社区的汽车则完好无损,于是,津巴多教授将停放在穷人社区的汽车的玻璃凿开一个大洞,结果该辆汽车也很快遭人损坏。[1]该实验表明,环境对行为人心理具有暗示性与引诱性,失序环境更易于诱发犯罪。
受此启发,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James Q.Wilsion)和凯林(George L.Kelling)于1982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警察和邻里安全:破窗》(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Broken Windows)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威尔逊和凯林认为,如果一栋房子的窗户破了,没有及时修补,更多的窗户将会被打破,久而久之就会给人一种混乱无序印象,大量违法犯罪由此滋生。该理论强调,环境具有极强的诱导性,假如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2]概括而言,破窗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意涵:
第一,无序与犯罪存在明显的关联性。破窗理论认为,无序环境对个人行为具有极强的诱导性,向民众传递出“此地犯罪控制较弱”的信号,并刺激其产生违法犯罪动机。[3]这一理论假设亦得到无数经验事实的佐证,譬如公园中的草坪被随意踩过之后,往往可能遭致更多人的踩踏;学校围墙被张贴广告之后,该墙面很快被广告覆盖。又譬如,秩序混乱城乡结合部,更易于沦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区”与“多发点”。[4]当然,并非所有的无序都会导致犯罪,而是“无序环境下诱发犯罪的可能性更大”[5]。
第二,无序必须突破“临界点”才能导致犯罪。尽管破窗理论承认无序与犯罪存在因果关联,但无序并不必然引发犯罪。换言之,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发生在无序处于相当的规模与程度,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才会出现。[6]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的失序行为,譬如随地便溺、公开醉酒、乱闯红灯、随手扔垃圾、性骚扰、街道涂鸦、强迫性乞讨、地铁逃票、收保护费等行为,虽然这些“轻微失序”并不必然引发犯罪,但当失序增量发展、累积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并达到“临界点”时,就会演变成犯罪。
第三,秩序维护(即“场域”控制)可有效防控犯罪。威尔逊和凯林认为:“不受管理和约束的失序行为,向民众传递出‘此处不安全’的信号,但这也给警方提供重要的政策暗示,因为维持秩序就能预防犯罪。”[7]根据破窗理论,维持秩序的方式主要包含“防破”与“补窗”两种,前者主要通过“秩序维护”方式将可能诱发犯罪的外部环境予以改善,而后者旨在通过“零容忍”方式高压打击违法犯罪,两者相得益彰,共同致力于防控犯罪。
(二)破窗理论的实践应用
事实上,破窗理论的提出并未立即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不少质疑。芝加哥大学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教授在《秩序的幻觉》(Illusion of Order)一书中指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与破窗理论的实施有关”[8];天普大学教授泰勒(Taylor)也认为“破窗理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的犯罪成因,也难以防范全部犯罪”。[9]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破窗理论被成功运用到纽约地铁与市区治安的犯罪防控之后才声誉大振,并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开展警务活动与犯罪防控的重要策略。
第一,破窗理论在美国的“试水”。为解决地铁内涂鸦、逃票、游民、醉酒、骚扰、强行乞讨、随地便秘等失序问题,纽约市捷运局于1990年率先引入破窗理论,先后实施以“秩序维护”为目标的“清洁列车方案”(Clean Car Program)与“收复地铁计划”(Recover Subway Plan),纽约市的地铁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地铁重罪发生率亦大幅度降低。紧接着,破窗理论很快被运用于纽约的城市治安与犯罪防控,对可能诱发犯罪的“轻微失序”进行清理与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美国司法部的资料显示,从1993年至1999年,纽约市的谋杀犯罪率下降了40%,抢劫罪发生率下降了30%,入室盗窃罪发生率下降了25%。[10]其中,自1991年到1994年四年间,纽约市的财产犯罪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由于应用效果明显,破窗理论及其衍生的“零容忍”政策逐步扩展应用于防控毒品犯罪、环境犯罪、强奸犯罪、学校暴力、种族犯罪等领域,至今仍作为美国犯罪预防的主流理论之一。
第二,破窗理论在其他国家(地区)的“推广”。除了美国,破窗理论及其衍生的“零容忍”政策在英国、中国等国家亦得到成功复制。为有效防控犯罪,英国哈特波市(Hartlepool)克莱威兰警察局于1994年引入了破窗理论及其“零容忍”策略。实施一年多来,其成效明显,整体犯罪率下降45%,一般盗窃案犯罪率降低71.5%,汽车盗窃案犯罪率降低68%,一般刑事犯罪率降低63.5%。[11]1996年12月,伦敦市王十字地区警察局对市区内的“轻微失序”(即乞丐、游民、公开酗酒等)也采取“零容忍”策略。在新加坡与我国香港地区,破窗理论及其“零容忍”政策也被广泛应用于反腐。譬如,香港廉政公署以“零容忍”姿态回应任何贪腐行为,公职人员就算贪污一块钱也要受到严厉的刑事惩罚。[12]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地区之一,与两地政府推行的反腐“零容忍”策略无不紧密相关。
二、环境犯罪中“破窗效应”的实证检视
破窗理论及其衍生的“零容忍”策略在英美等国家或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为防范特定环境中的犯罪以及利用特定环境控制犯罪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知识借鉴。但在我国环境犯罪防控领域,“破窗效应”是否存在,有哪些表征以及如何引发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极少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发布的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冀望通过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的方式发现、揭示以及论证环境犯罪中的“破窗效应”。
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两高”先后发布了5批共48个环境典型案例,其中涉及环境犯罪的有29个,但与环境污染犯罪相关的仅有13个。从这13个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领域广泛存在,环境污染向环境犯罪演变过程中往往存在“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具体表现为以下三大效应:
(一)首窗效应
破窗理论认为,“第一扇破窗”常常是事情恶化的起点,这一现象在“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中得到充分验证。根据下表1可知,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往往存在“第一扇破窗”。譬如,在案例1紫金山铜矿污染事故中,该事故的“首扇破窗”为2006年“涵洞渗漏事件”;在案例8洛阳东川“牛奶河”事件中,该事件的“首扇破窗”是塑料厂的违法排污等等。不受管理和约束的排污行为,实际上就是“第一扇破窗”。如若环境污染的“第一扇破窗”得不到及时修补,将引发更多违法排污行为,直至演变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与津多巴“偷车实验”所得出的结论高度吻合,同时也解释了预防“第一扇破窗”的重要性。
(二)累积效应
环境污染往往存在质变到量变的过程,一个、两个或三个轻微环境污染行为固然不会轻易引发环境犯罪,而当这些不良现象大量、频繁和集中的出现时,便可能诱发环境污染事故。在案例1中,紫金矿业公司从2006年出现渗漏便连年整改,但由于整改不力,最终于2010年酿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在案例5中,徐有等人连续12次跨区倾倒危险废弃物,结果造成地下水的严重污染;在案例10中,内蒙古、甘肃、宁夏部分企业从2010年开始便持续向腾格里沙漠排放工业废水,由于环境污染不断增量发展,超过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最终于2014年引发严重沙漠污染。可见,环境污染事故并非总是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排污、不断累积且得不到有效整治后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三)耦合效应
考察下表1的相关案例可知,环境污染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存在明显的共生性。在案例2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污染事故案中,3名环保官员因监管失职被立案侦查;在案例7广西龙江镉污染案中,河池市环保局副局长曾觉发因受贿被刑事追诉。此外,考察其他的典型案例亦可发现,环境污染事故的背后均存在环境监管失职渎职的影子。诚然,若环境监管部门严格执法、依法移送涉罪案件,则企业对违法排污必将有所忌惮;若环境监管部门疏于监管、以罚代刑,则被企业视为对违法排污的默许与纵容。由此推知,环境污染事故的出现大多是企业违法排污与监管失职渎职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表1“两高”公布的13个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要点凝练
┌──┬──────┬───────┬──────┬───────┬──────┐
│编 │案例 │污染行为 │补救措施 │监管概况 │环境污染之“│
│号 │ │ │ │ │首 │
│ │ │ │ │ │扇破窗” │
├──┼──────┼───────┼──────┼───────┼──────┤
│1 │紫金矿业集团│清污分流涵洞渗│2006年—2010│监管部门对污染│2006年“涵洞│
│ │股份有限公司│漏、非法偷排,│年,每年都在│未加制止,环保│渗漏事件” │
│ │紫金山金铜矿│造成水体严重污│整改 │局长等因监管失│ │
│ │重大环境污染│染 │ │职、贪腐被立案│ │
│ │事故案 │ │ │调查 │ │
├──┼──────┼───────┼──────┼───────┼──────┤
│2 │云南澄江锦业│富含砷的废水渗│2005年—2008│3名环保官员因 │2005年,公司│
│ │工贸有限责任│入地下水,导致│年,经多次处│监管失职被立案│私设暗管排放│
│ │公司重大环境│湖泊被砷污染 │罚仍不整改 │ │含砷工业废水│
│ │污染事故案 │ │ │ │ │
├──┼──────┼───────┼──────┼───────┼──────┤
│3 │重庆云光化工│非法倾倒危险废│交不具资质的│缺 │缺 │
│ │有限公司等污│物 │张必宾处置 │ │ │
│ │染环境案 │ │ │ │ │
├──┼──────┼───────┼──────┼───────┼──────┤
│4 │胡文标、丁月│非法排放含苯、│2007年—2009│涉污企业被认定│2007年,胡文│
│ │生投放危险物│酚等有毒物质的│年持续排放废│为“废水不外排│标 │
│ │质案 │废水 │水,未采取补│企业,政府疏于│”等人故意排│
│ │ │ │救措施 │监管 │放含毒废水入│
│ │ │ │ │ │五支河 │
├──┼──────┼───────┼──────┼───────┼──────┤
│5 │徐有等3人污 │危险废物跨区转│缺 │缺 │2013年1月, │
│ │染环境案 │移倾倒,持续12│ │ │徐 │
│ │ │次倾倒 │ │ │有等人夜间跨│
│ │ │ │ │ │区倾倒废物 │
└──┴──────┴───────┴──────┴───────┴──────┘
┌──┬──────┬───────┬──────┬───────┬──────┐
│编 │案例 │污染行为 │补救措施 │监管概况 │环境污染之“│
│号 │ │ │ │ │首 │
│ │ │ │ │ │扇破窗” │
├──┼──────┼───────┼──────┼───────┼──────┤
│6 │郭某甲涉嫌污│违法排放含有毒│缺 │执法部门“有案│2013年10月,│
│ │染环境案等5 │物质污水,仅郭│ │不移”,检察部│郭某甲直排含│
│ │起案件 │某甲就排放四五│ │门介入开展立案│毒废水 │
│ │ │十吨 │ │侦查 │ │
├──┼──────┼───────┼──────┼───────┼──────┤
│7 │曾觉发环境监│广西龙江镉污染│涉污企业对整│河池市环保局副│2010年6月, │
│ │管失职、受贿│ │改通知未理会│局长曾觉发监管│广 │
│ │案 │ │ │失职,受贿4.5 │西金河公司违│
│ │ │ │ │万元 │法堆放矿渣,│
│ │ │ │ │ │存 │
│ │ │ │ │ │巨大隐患 │
├──┼──────┼───────┼──────┼───────┼──────┤
│8 │李明坤玩忽职│企业非法排放废│缺 │监察部门未认真│2009年6月, │
│ │守案 │水、废渣,导致│ │履行职责,监管│企业向小江非│
│ │ │东川“牛奶河”│ │不力,检察机关│法排污、违法│
│ │ │事件 │ │介入侦办 │生产 │
├──┼──────┼───────┼──────┼───────┼──────┤
│9 │谢云东、孙普│塑料厂长期将红│缺 │环保局官员存在│塑料厂违规经│
│ │伟玩忽职守案│色染料排入涧 │ │渎职,检察机关│营、非法排污│
│ │ │河,色素超标10│ │介入予以严查 │ │
│ │ │倍,酿成“红河│ │ │ │
│ │ │谷”事件 │ │ │ │
├──┼──────┼───────┼──────┼───────┼──────┤
│10 │最高检挂牌督│内蒙古、甘肃、│经多次整改,│监管部门虽进行│2010年宁夏中│
│ │办4起腾格里 │宁夏部分企业长│但依旧暗设管│整改与处罚,但│卫造纸厂“沙│
│ │沙漠污染环境│期向腾格里沙漠│道进行非法排│环境监管失职、│漠偷排”事件│
│ │案 │排放废水 │污 │渎职严重 │ │
├──┼──────┼───────┼──────┼───────┼──────┤
│11 │赵大闯等人污│化工长挖1500立│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以没有│2014年3月, │
│ │染环境案 │方米渗坑排放污│迁 │污染鉴定为由不│赵 │
│ │ │染物 │厂后继续非法│予立案 │大闯等人挖渗│
│ │ │ │排污 │ │坑排污 │
├──┼──────┼───────┼──────┼───────┼──────┤
│12 │倪可佃等3人 │2012年—2014 │缺 │环境执法人员严│2012年7月, │
│ │环境监管失职│年,永丰化工公│ │重不负责任,未│永 │
│ │案 │司超长期标排污│ │及时发现污染并│丰化工公司违│
│ │ │ │ │企业排污 │法建厂、超标│
│ │ │ │ │ │排污 │
├──┼──────┼───────┼──────┼───────┼──────┤
│13 │张建强环境监│2009年—2011 │缺 │环境监察大队长│2009年,洗钨│
│ │管失职案 │年,洗钨场非法│ │张建强长期“以│矿场非法经营│
│ │ │经营、长期排污│ │罚代管”,严重│ │
│ │ │ │ │渎职 │ │
└──┴──────┴───────┴──────┴───────┴──────┘
三、环境犯罪中“破窗效应”的逻辑证成
透过对“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可知,轻微环境污染向环境犯罪演变过程中大多存在“破窗”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往往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特别是排污企业)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从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环境监管者对此应予以足够警惕。
(一)直觉思维
以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再次考察“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在企业违法排污冲动与排污行为作出之间存在着一个“认知加工通道”。该通道常常借助于人类特有的两种信息处理系统(机制)发生作用:一种是“经验—直觉”信息加工系统,该系统不受理性意识的束缚,只需占用少量资源,行为人便可凭借个体经验快速、自动的处理信息[13];另一种是“理性—分析”信息加工系统,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能理智地对待问题、运行概念、识别规则,有意识的解决和处理问题[14]。因而在心理学中,“经验—直觉”系统往往被视为第一系统,而“理性—分析”系统被视为第二系统,第一系统中的经验与直觉具有先行作用,特别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个人直觉可以凭借经验对不确定事件作出评估与判断。这在环境犯罪领域同样如此,排污企业习惯于依靠自身经验的直觉机制作出违法排污的判断与决策。譬如在上表1的案例10中,宁夏中卫明盛染化公司等多家企业之所以无所顾忌的向腾格里沙漠排污,无非在“经验—直觉”的影响下笃信沙漠可大量沉降污水,且该行为能有效逃避监管,这同时也符合“有限理性”的认知规则。
诚然,宁夏中卫明盛染化公司的违法排污是一种基于“经验—直觉”认知机制而作出决定,尽管游离在企业理性选择之外,也偏离了环境监管的应然目标,但这种直接思维机制却大量存在,成为部分企业解决实际排污问题的常备手段。事实上,企业排污直觉思维极易诱发“破窗效应”,当环境污染之“窗户”被频繁打破时,不但难以得到修补,还可能引发“破窗”式的连锁效应,毕竟放任“破窗”符合企业违法排污的心理预期,也是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遵循有限理性法则的体现。当企业受“经验—直觉”认知机制支配时,其“理性—分析”信息加工系统就会遭受抑制,而难以作出理性决策。在上表案例11中,赵大闯等人因挖渗坑排污被举报后不但没有痛改前非,而且还选择迁厂继续违法排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赵大闯等人已形成对环境执法能力偏弱的直观认知;另一方面,“环境违法成本低”已内化外为“经验之谈”,行为人笃信不疑。可见,当个人行为受“经验—直觉”机制支配时,环境违法犯罪的大量滋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行为惯性
行为惯性是一种逻辑自动化的行为机制,即“只要一定的引发条件出现,就会反射性地产生”[15]。在心理学家看来,人类的行为逻辑并非完全理性的,也不都是严格遵循三段论的形式推理规则,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经验—直觉”式的推理规则。尽管这种行为逻辑并不完全有效,但却是行为人在占有少量信息资源下解决实际问题的优先选择。而人类固有的模仿天性更强化了这种行为惯性,特别是在信息匮乏或群体行动中,人类往往选择非理性模仿或盲目遵循集体行动逻辑。这一观点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论证,譬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和微生物一样强大的传染力。”[16]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提出:“自杀(行为)可以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自杀的产生可部分归因于效仿。”[17]由此可见,人类在自身模仿天性与群体行动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个人行为可能呈现出盲从、因袭等惯性特征。
破窗理论认为,外在环境具有强烈地暗示性与诱导性,失序环境易于诱发犯罪。行为人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暗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一些潜在的观念进入大脑后容易支配个人行动,甚至固化为行为惯性。在环境监管过程中,企业亦普遍存在着盲从的行为惯性,“受从众的影响,个人会接受同伴的行为,导致行为同质化”[18],譬如当一家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受放纵时,可能给其社会公众传递出“环境污染不受规制”的信号,结果势必引起其他企业的非理性效仿,这也正如勒庞所言“传染的威力甚大,犯罪群体易受怂恿,轻信和易变”[19]。长此以往,“环境违法成本低”、“违法排污不受规制”等不良观念必将深植于企业者内心深处,在“经验—直觉”机制的作用下驱动行为人违法排污。由此观之,企业在不良排污观念以及固有模仿天性的影响下,容易养成放纵“破窗”的行为惯性。
(三)风险认知
个人在作出某一行为之前,往往根据一些容易获知、明示但未必准确的信息在判断违法风险的大小。但由于信息的匮乏或不对称,行为人容易根据“容易获知的关于社会秩序安全的外在信息来推断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大小与他人是否同等遵守法律,并由此对违法犯罪的制裁风险作出错误假定”[20],换言之,公众对某一行为的风险判断取决于对外在信息的认知加工流畅程度,“高流畅度带来趋于正面的判断,低流畅度带来趋于负面的判断”[21]。这在环境监管领域同样如此,假定环境执法力量强大、公众监督机制完善且社会控制井然有序,那么企业将会作出“环境违法风险高”的推断;若环境执法不严、执法威慑性弱且社会监督机制不全,则给人一种“社会控制较弱”的心理暗示,促使排污企业形成“环境违法风险低”的推断。
事实上,“由于政府的执法效率低下以及暴力制裁符号价值的弱化,普遍的守法就不可能建立在公民对实际法律制裁风险的理性认知上”[22]。诚然,在有限理性与信息匮乏的作用下,排污企业很难提高对违法风险的主观认知,再加之环境监管失职渎职的普遍存在(参见上表1中案例),无疑进一步刺激与放纵了企业的违法排污冲动。由此观之,在信息不对称性的情况下,企业对排污风险容易造成认知偏差,使“环境违法风险低”成为其内心信条,即便出现“第一扇破窗”,排污企业也缺乏修补“破窗”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久而久之,环境污染的“破窗”不断升级,最终诱发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故此,环境犯罪的防控应当注重改善可能诱发犯罪的物理环境(即“场域”),在有效干预潜在排污者的心理、动机以及行为的基础上减少环境违法犯罪。
四、环境犯罪的“场域控制”及其策略选择
行文于此,可知破窗理论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改善“犯罪场域”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这对环境犯罪防控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应当注重改善可能诱发环境犯罪的“场域”(即外在物理环境),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同时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策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以有效防控环境犯罪。
(一)引入“情境预防”策略
根据破窗理论,犯罪防控的重中之重在于“防破”,即改善可能引发环境犯罪的外在环境,故此应当对环境犯罪实行“情境预防”。“情境预防”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犯罪学家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Clark)提出,他在《情境犯罪预防——成功案例研究》一书中罗列了12种情境犯罪预防技术,主张通过对“轻微失序”行为进行针对性的“技术控制”,以期在改善微观环境的基础上防范违法犯罪。概言之,环境犯罪的“情境预防”可通过以下三个方案实现:
第一,目标加固方案:提高环境犯罪难度。克拉克认为,“情境预防”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目标加固”的方式使犯罪更加困难,譬如在小汽车上装警报装置、防盗玻璃,在住宅区安装附加锁等,以有效遏制犯罪。[23]事实上,犯罪的容易程度、机会大小、条件是否成就等因素对潜在犯罪者的犯罪决策均具有重要影响,“目标越是容易接近越可能成为犯罪的对象,如陈列在商店外面的货物,或者夜深游荡在偏僻街区上的行人都具有犯罪的易接近性”[24]。在环境监管过程中,亦可采取一些技术性举措,通过减少企业污染环境机会性与提升环境违法难度性的方式,物理性的阻却环境犯罪的发生。譬如,安装自行监控设备、发布环境信息月报、加强对重点企业的风险评估、设立环保举报热线、建立专业化与信息化管理机制,将科技手段转化为环保执行力,最终有效抑制企业的环境违法冲动。
第二,风险渐增方案:提升环境犯罪风险。破窗理论认为,城市的恶劣环境就像瘴气一样会使犯罪产生传染性。在环境监管领域,当“以罚代管”的不良信号无限扩散与弥漫之后,往往弱化企业对环境犯罪风险的主观认知,“环境违法风险低”的信号在相互传染中易于成为主流信条,最终引发企业对环境违法的争相效仿。对此,环保部门可因势利导调整环境执法策略,增强企业对环境犯罪风险的心理认知,放大环境执法的潜在威慑性。譬如通过增加环境监察频率、强化不定期监察、规范典型案例指导等方式,确保企业有效认知环境违法的潜在风险。当企业容易获得“环境违法风险高”等外在信息时,无疑将会对自身行为予以约束。尽管“增加风险认知”仅仅是一种视觉管理策略,但是往往可以对潜在环境犯罪者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这与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主张的“酷刑的视觉威慑”[25]莫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收益剧减方案:降低环境犯罪报酬。根据“情境预防”理论,降低犯罪报酬可一定程度减少违法犯罪案发率,譬如加强税务申报、清洗乱刻乱画、制作“防游民”长椅等。这一犯罪防控思路得到了美国学者阿曼达·多蒂(Amanda Doty)的认可,他认为,“破窗理论可应用于环境犯罪没收法,即通过没收制造环境污染的工具和设施(譬如非法倾倒垃圾的车辆),减少环境违法犯罪的预期收益。[26]这一犯罪防控举措亦可资我国借鉴,倒逼企业自觉守法。除此之外,我国环保部门应转变其惯常的“以罚代治”思维,合理运用查封扣押、排污权交易、行政代履行等监管手段,将违法排污的潜在收益降至最低乃至无利可图,从而督促企业自行履行治污义务,亦或是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
(二)确立“零容忍”策略
环境犯罪既要立足于“防”,也要强化于“控”,惟有打出“防”与“控”的“组合拳”,才能形成打击环境犯罪的合力。根据“零容忍”政策,姑息与放纵轻微违法均可能滋生严重犯罪,对此应当对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以有效震慑潜在犯罪者。然而,“重刑而连其罪”[27]之铁腕治污远不足以惩治环境违法犯罪,还需引入第三方治污模式,将“补窗”方式更为多样化。
第一,“严打”轻微环境违法行为。破窗理论认为,为有效规避“破窗效应”,应注重整治可能诱发犯罪的轻微失序行为。环境监管中的失序行为,譬如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罚款了事、偷排偷放、非法倾倒、超标排污等均可能成为环境犯罪的诱因,倘若放任这些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无异于变相鼓励和纵容环境污染。鉴于此,国务院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2014)以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均要求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譬如,健全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与倒查机制,亦督促环境执法人员自觉守法;加强对环境污染犯罪认定中的模糊概念(如严重后果、重大事故等)予以进一步明晰;适当降低环境监管失职罪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入罪门槛,加强对环境监管失职渎职行为的刑事追究。
第二,健全环境“两法衔接”机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韦斯利·斯高根(Wesley G.Skogan)在《失序与衰退》一文中明确指出:“诱发严重犯罪的‘破窗’,应当及时修补。”[28]诚然,惟有及时“补窗”,才能避免“破窗”式的连锁效应。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破窗”不断,环境污染事故处于一种高发与频发态势,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9]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3年,全国共发生了2216起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平均每年发生554起,但同期每年作出的环境刑事判决却寥若晨星。环境污染事故鲜有入刑,不仅放任了“第一扇破窗”的发生,还直接刺激了“破窗”的升级。因此为防范“破窗效应”,亟需健全环境“两法衔接”机制,确保每一起涉环境犯罪案件都能已送至刑事司法领域,借助刑事司法手段及时“补窗”,从而有效震慑潜在的环境犯罪者。
(三)构建第三方治污模式
确立“零容忍”政策,并非一味的严打环境污染行为,毕竟“层层加码式”的惩治策略并不可行,还可能引发排污企业的强烈抵触与抗拒,结果势必影响环境监管的实际效果。故此,中国式的“补窗”方案不应徘徊于政府的高压打击与企业的自觉守法之间,还应引入第三方协助“补窗”,即构建第三方治污模式。第三方治污是公私协作的形式之一,有助于将复杂、专业的治污任务交予市场上的专业公司履行,而排污企业只需缴纳一定的代清理费用即可。在第三方治污过程中,政府扮演居中监管的角色,虽然不直接参与代清理工作,但负责代清理费执行等相关事项的监督,为第三方治污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第三方治污模式的引入,使得环境污染的“补窗”方式更为灵活性、多样性、专业性与实效性,从而真正实现环境污染的“零容忍”。
【注释】
[1] Philip G. Zimbardo: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17).P.237-307.
[2][美]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陈智文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5页.
[3] Michael Wagers, 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Willan Publishing; 2008.P.257-258.
[4]马少春,王发曾:《城乡结合部的犯罪机会控制与空间综合治理》,《人文地理》2012年第2期。
[5]楼伯坤,满涛:《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基于“破窗理论”的本土化思考》,《犯罪研究2013年第6期。
[6] Michael Wagers, William Sousa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Willan Publishing; 2008.P.258.
[7][美]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陈智文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5页。
[8] Bernard E.Harcourt: Illusion of Order: The False Promise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78-80.
[9] Ralph B.Taylor: Breaking Away from Broken Windows: Baltimore Neighborhoods and the Nationwide Fight against Crime, Grime, Fear, and Decline; Westview Press; 2001.P.39-107.
[10] Dan M.Kahan: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Meaning, and Deterrence; Virginia Law Review; 1997(3).PP.367-380.
[11]杨爱华,李小红:《破窗理论与反腐败“零度容忍”预惩机制》,《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4期。
[12]郭媛丹:《零度容忍:贪一块钱也不行》,载《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2日版。
[13]参见杨群,邱江,张庆林:《演绎推理的认知和脑机制研究述评》,《心理科学》2009年第3期。
[14] Win De Neys: “Bias and Conflict: A Case for Logical Intuitions”;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1).PP.12-34.
[15] John A. Bargh and Erin L. Williams: The Automaticity of Social life; Current Direction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3).P.1-39.
[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1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8页。
[18][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129页。
[1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20]伍德志:《论破窗效应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1]李学尧:《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2]伍德志:《论破窗效应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3]参见刘晓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犯罪研究》2009年第6期。
[24]庄劲,廖万里:《犯罪预防体系的第三支柱—西方国家犯罪情境预防的策略》,《犯罪研究》2005年第2期。
[25]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26] See Amanda Doty: Reshaping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How Forfeiture Statutes Can Deter Crime;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06(18).PP.521-542.
[27]《商君书》.石磊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页。
[28] See Wesley G.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Free Press; 1990.P.70-75.
[29]环保部:《全国环境统计公报》,http://www.zhb.gov.cn/zwgk/hjtj/qghjtjgb/,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07月23日。
【作者简介】蒋云飞,重庆大学法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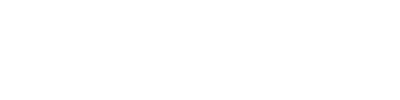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