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凡
【摘要】 美国在其《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创设了一项新的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允许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直接起诉“恐怖主义资助国”以获得民事赔偿。在国内法层面,该项国家豁免例外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了追究“恐怖主义资助国”责任的法律途径;在国际法层面,其作为一国的反恐单边措施,势必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家行为和责任承担,且可能因当前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需求而被更多的国家认可和效法,值得加以关注。
【关键词】 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受害者;民事诉讼;民事赔偿
一 引言
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和持续性地区冲突,促使以中东、南亚和非洲为主要策源地的恐怖主义浪潮兴起,日趋蔓延至全球各地。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恐怖主义跨境流动频繁,其思想和人员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迅速扩散;二是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日益转向平民。[1]数据显示,2015年因恐怖主义袭击致死的3.5万人中,绝大多数为普通民众。[2]面对恐怖主义蔓延的严峻态势及其带来的危害,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并保护受害者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
传统上,国家回应恐怖主义的措施可分为武力和非武力两种模式。前者是国家通过单边或联合军事行动,直接摧毁恐怖主义人员及其基础设施;后者则包括国家通过经济制裁阻止恐怖主义人员获得武器和资金,以及通过刑法直接惩罚恐怖主义行为人。这些措施主要致力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本身,而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的事后法律救济则明显不足。在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日益转向平民的新形势下,国家需要在传统反恐措施的基础之上寻找其他有效应对方式。
美国近年来启动了国内民事诉讼反恐措施,允许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恐怖主义资助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措施旨在让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民事赔偿,并进一步摧垮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资助者的资金供给能力。然而,当资助恐怖主义的主体是一个主权国家时,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的国家豁免规则会阻碍该项措施的实施。为解决这一法律问题,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司法判例,最终于2008年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创设了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赋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直接起诉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权利。
本文以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为基础,分析以民事诉讼方式来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国内司法救济的利弊,以及该措施在当前国际法上的效力,以期为我国完善反恐立法体系、保护公民海外安全和利益提供借鉴。
二 《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
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规则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法院通过案例法确定外国主权享有绝对豁免,到联邦政府决定外国主权豁免问题,再到通过单项立法确立限制豁免原则。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特定历史环境对外国主权豁免规则产生的影响。起初,美国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外国主权实行绝对豁免。例如,在“舒纳诉麦克法登案”中,两个美国公民对被法国军队征用后因天气原因滞留在费城港口的一艘船发生所有权纠纷,马歇尔法官出于对法国主权的尊重,拒绝受理此案。他认为该船构成美国行使领土管辖权的一个例外,因为“不同主权之间完全的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使得将一国置于另一国的管辖之下与其尊严不符”。[3]1952年,美国国务院致函司法部表示,因国家参与商业活动日益增多,需要法院保护与国家进行交易的私人权利,因此美国对外国主权宜采用限制豁免,即对外国国家公法行为(jure imperii)给予豁免,而对外国参与商贸等私法行为(jure gestionis)不再给予豁免,美国法院可以对其行使管辖权。[4]该信函没有具体解释如何区分国家的公、私法行为。实践中,美国联邦政府依据外国国家行为的具体情况作出是否享有管辖权的决定。由于国家豁免问题经常受到当事国的外交压力,在此时期美国政府作出的豁免决定被指责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5]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旨在以立法形式统一美国对外国主权豁免的标准。该法以“原则豁免,例外排除”的立法模式,规定外国在美国原则上享有主权豁免,但其“商业行为”等法定例外情形除外。
(一)《外国主权豁免法》增设“恐怖主义例外”的缘由
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没有涉及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豁免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该问题凸显。1988年12月洛克比空难发生后,美国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该法规定,任何因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和商业损失的美国公民或其继承人可以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获得三倍的赔偿金和诉讼费用。但该法没有明确,当资助恐怖主义的主体是一个主权国家时,该主权国家是否可以成为被告。在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起诉利比亚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认为《反恐怖主义法》并未规定主权国家可以依据该法成为被告,而恐怖主义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亦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已有规定的豁免例外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在“原则豁免,例外排除”的立法模式下,如果没有法定例外情形出现,外国的国家行为就享有豁免。法院由此驳回了受害者家属的起诉。[6]
1995年,美国女大学生艾丽萨·弗莱托(Alisa Flatow)在以色列一辆游览车中被附近发生的恐怖性自杀爆炸致死,其家属在起诉涉嫌资助该恐怖事件的伊朗时,同样遇到来自《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法律障碍。在弗莱托家属积极推动下,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与有效死刑法》。该法规定,对于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国家,当其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导致美国公民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该国在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不享有豁免。[7]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恐怖主义资助国行为的民事责任法》,即通称的《弗莱托修正案》。该法允许发生在美国境外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在诉讼中寻求惩罚性赔偿。[8]《弗莱托修正案》通过后,美国联邦法院受理了弗莱托家属起诉伊朗的案件。[9]但在对其他外国涉嫌资助恐怖主义的诉讼中,美国各地法院对《弗莱托修正案》是否赋予了个人直接起诉“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权利存在不同理解。[10]
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澄清了其立法意图。[11]该法明确规定,个人可以直接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以获得民事赔偿。该规定作为一项新的国家豁免例外纳入《外国主权豁免法》,替代先前《反恐怖主义与有效死刑法》中关于“恐怖主义”民事诉讼的规定。[12]
(二)《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具体内容
依据该项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外国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的酷刑、法外处决、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行为,或为上述行为提供资助所导致的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失,在受害者对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该国在美国法院不享有豁免。[13]针对上述行为的民事诉讼,只要是在有效期限内提起,且所诉外国已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美国法院即应受理。[14]
“恐怖主义例外”下的民事诉讼,原告可以是受害者或者代表受害者的其他申诉人。在所诉恐怖主义行为发生时,原告须是美国公民、美国军队成员或在职责范围内行事的美国政府雇员或者执行政府合同的个人。[15]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可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非美国籍家庭成员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例如,在“莱博维奇诉伊朗案”中,三岁的美国公民莱博维奇随家人在以色列旅行时遭遇巴勒斯坦穆斯林组织炮弹袭击;莱博维奇严重受伤,同在车上的外祖父母和两个姐妹(非美国公民)见证了莱博维奇所受伤害。他们回到美国后起诉涉嫌资助此次袭击行为的伊朗,要求其对车上每位家庭成员的伤害予以赔偿。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下,法院的管辖权涵盖美国公民的外国家庭成员因美国公民遭受恐怖主义伤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16]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外国”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立法上,其涵盖三类主体,即外国国家本身(the state itself)、外国国家的政治分支(a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a foreign state)以及外国国家的代理人或工具(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a foreign state)。在“弗莱托诉伊朗案”中,原告起诉的被告包括伊朗、伊朗信息与安全部、伊朗前总统、伊朗信息与安全部前部长。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认为上述所有被告均符合《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并裁定伊朗与案中所诉的官员、雇员和代理人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7]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一个实体是否具构成《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外国”时,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1)创设这个实体是否具有国家目的;(2)该国是否为这个实体雇用公务员并支付工资;(3)该实体在国内是否拥有专属权利;(4)该实体在国内法上的主体地位。[18]在“阿拉伯船舶公司诉鹰牌系统公司”中,被告是一家依据条约由六个国家共有的合资公司。法院认为,虽然《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是“一个外国”的豁免问题,但该案中的合资公司构成该法所指的“外国”。[19]由此,“恐怖主义例外”下的被告范围除了立法上明确规定的国家本身、国家机关以及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为的官员、雇员或代理人,还涉及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认定并纳入“外国”范畴的其他相关实体。
三 《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国内实施
(一)“恐怖主义例外”下的判决执行
受害者及其家属依据“恐怖主义例外”获得胜诉后,通常难以直接从所诉外国获得判决的赔偿金额。一方面,现行国际条约和美国国内法保护外国国家财产免于扣押和执行;[20]另一方面,依据“恐怖主义例外”判决的案件所涉赔偿金额巨大,不易执行。在“恐怖主义例外”下,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的赔偿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部分。补偿性赔偿是对受害者因被告实施或资助的恐怖主义行为所遭受损失的赔偿,包括经济损失以及身体或精神伤害之抚慰金等。[21]惩罚性赔偿旨在震慑和惩罚被告,[22]因而数额往往较大。例如,在“弗莱托诉伊朗案”中,在专家提供的伊朗每年资助恐怖活动的预算基础上,法院按照三倍惩罚性赔偿原则,裁定伊朗对受害者承担惩罚性赔偿2.25亿美元。[23]
为解决判决执行难问题,美国国会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2000年,国会通过《人口贩运与暴力受害者保护法》,允许起诉伊朗资助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从美国政府控制的伊朗财产中获得赔偿。[24]2001年,国会通过《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允许法院将被美国政府冻结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财产用于执行判决。[25]2008年《国防授权法》进一步规定,对于外国在美国境内的商业用途财产以及外国机关或代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财产,在法定情形下可以扣押或用于执行美国法院判决。[26]与此同时,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该法还专门规定,在诉讼提起之时,对作为被告的外国有形或无形财产自动设立留置权。[27]
近年,判决执行问题直接引发了新的诉讼。在“伊朗中央银行诉皮特森案”中,依据“恐怖主义例外”胜诉的受害者试图对伊朗中央银行在纽约一个证券账号内的17.5亿美元债券实施强制措施,该债券是伊朗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在执行未决时,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联邦地区法院扣押该17.5亿美元债券,用于赔偿伊朗所支持的恐怖主义事件的受害者。[28]伊朗中央银行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会通过专项立法直接影响一个未决案件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2016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有权通过立法规制一个或多个具体事项,因此这项法案没有违反三权分立原则。[29]据此,伊朗中央银行的这部分债券将可能用于执行美国法院的判决。目前伊朗已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此举违反双方签署的友好协定,国际法院亦已受理。[30]
(二)支持与反对“恐怖主义例外”的观点
支持者主张将《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恐怖主义例外”适用于所有外国,而不限于目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上的国家。[31]该主张得到9.11恐怖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推动。2016年9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法》,将其作为“恐怖主义例外”之后的一项条款,授权美国联邦法院受理针对外国实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及其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在美国境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民事诉讼。[32]从该条款的字面含义看,任何“外国”实施了上述行为均有可能在美国联邦法院被起诉。依据此条款,9.11恐怖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正准备起诉涉嫌资助此次事件的沙特阿拉伯。鉴于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同盟国,法院如何解释和适用此条款将备受关注。[33]
反对者则认为实施“恐怖主义例外”的成本过高,其立法目的也难以完全实现。首先,该项措施制约了政府的外交政策。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起诉外国的案件一旦进入美国司法程序,政府就难以控制其结果,而法院又不具备评估其判决给外交政策所造成影响之能力,导致判决妨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其次,依据“恐怖主义例外”受理之案件的被告多远离美国本土,通常在审判中缺席,法院只能依据原告的指控作出判决,难以起到震慑被告的效果。最后,虽然此类诉讼给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了一个在法庭上澄清事实和获得赔偿的机会,法院也可以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扣押或执行被告在美国的财产,但是能被法院扣押和执行的外国财产相较于判决中的巨额赔偿还是太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多项改善措施。例如,有学者建议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起诉相关外国之前先向美国政府部门提出申诉,由政府部门对外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只有政府部门无法解决赔偿问题时,受害者及其家属才可到法院起诉,以减少民事诉讼给政府外交政策带来的制约。[34]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有学者建议废除“恐怖主义例外”下的惩罚性赔偿,以减少被诉外国对巨额赔偿的抵制。[35]此外还有学者担心,“恐怖主义例外”会导致外国制定对等立法,取消美国在其境内的主权豁免,国际习惯法上的主权豁免原则会在这种“没有节制”的恐怖主义例外下遭到破坏。[36]有鉴于此,“恐怖主义例外”的适用需要一定限制。
(三)“恐怖主义例外”实施中的调控机制
目前,《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仅适用于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主义资助国”政府定期调整名单上的国家,以使被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及时反映政府外交导向。此外,在依据“恐怖主义例外”所提起之民事诉讼的取证过程中,若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认为取证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或未决刑事案件程序,则其有权随时中止取证程序。[37]这一措施旨在解决具体案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
《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法》通过后,被起诉的涉嫌恐怖主义资助国的范围是否会迅速扩展至上述名单之外的国家?这一问题引起了各国关注。该法中的一项条款已经授予美国司法部介入此类诉讼程序的权利,即若司法部证明美国政府正在与涉案外国就赔偿问题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则法院可以暂停针对该外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程序。[38]鉴于该法对美国外交的潜在影响,美国国会很可能会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其适用范围。[39]
四 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上的效力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意指未经一国同意,该国免受另一国家国内法院的管辖。《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恐怖主义例外”限制了相关外国的豁免权,允许美国国内法院受理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对主权国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作为一项单边措施,它势必影响相关国家的国家行为和责任承担。那么,在国际法上如何评价此种单边措施的效力?下文将就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家豁免规则的演变趋势
国家豁免规则体现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前者包括1972年生效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200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相关家豁免习惯法;后者则体现为各国相关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如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加拿大1985年《国家豁免法》等。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通常不仅体现一国对国际法规则本身内容的理解,还融合了其国内立场选择,特别是国内宪法原则方面的考虑。在2012年“德国诉意大利国家豁免案”中,国际法院认定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国家行为在现行国际习惯法下仍享有豁免,但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这一国家豁免习惯法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保护的个人诉诸司法之基本权利相冲突,因而拒绝将其纳入意大利国内法体系。[40]美国最高法院则主张外国主权豁免,在普通法和现行《外国主权豁免法》之下,始终是恩赐和礼让,而不是一项法律上的权利。”[41]其因此认为,外国主权豁免并非不可减损,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对某一外国限制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所给予的国家豁免。
虽然各国对国家豁免的具体适用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豁免规则从最初的绝对豁免到目前广为适用的限制豁免这一演变历程,反映出其适用范围日益限缩的趋势。根据国家实践的需要,新的国家豁免规则会不断出现。与其他国际规则发展模式一样,新的国家豁免规则往往会首先出现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国内法层面上,随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效法,从而发展成为国际法规则。[42]
(二)国际法对“恐怖主义”的规制
恐怖主义早已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谴责。国际法上业已形成由13个国际条约及三个补充议定书组成的反恐条约体系,对劫持人质、劫持航空器、恐怖主义爆炸、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等特定领域的恐怖注意活动作出“或起诉或引渡”的明确规定。[43]此外,联合国在《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中提出:“成员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的,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戒除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在他国领土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戒除默许或鼓励在其本国境内以上述行为为目的的行为。”[44]9.11事件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和充分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并且“有必要在其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手段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45]
2015年11月巴黎恐怖事件之后,安理会重申“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一个威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在何地、何时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46]并要求“所有成员国按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依其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及遏制决议中涵盖的恐怖主义行为”。[47]
上述国际反恐条约、联合国宣言及安理会决议为国家的反恐措施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支持。不过,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而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法律途径则相对关注较少。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对恐怖主义是否构成国际罪行也看法不一。[48]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国采取的单边措施,“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层面上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
(三)“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上的效力
人们常用“合法”或“非法”来评价一国实施的单边措施在国际法上的效力。然而,在一些国际法规则缺失、不明确,或者相关国际法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对国家实施的单边措施就很难用单一的、非白即黑的“合法”或“非法”来判定其在国际法上的效力,而是需要更具体的标准。
1.国家单边措施的可实施性
在1951年“英国诉挪威捕鱼案”中,国际法院最先使用“opposable”(法语,相对应的英语为enforceable )标准来评价在国际法规则缺失、不明确的领域内,一国对另一国所实施之单边措施的效力。[49]该案中,国际法院认为英国关于北海的立场及其长期的弃权使得挪威运用“海湾口10海里直线规则”划定双方在北海的领土水域对英国具有可实施性。在1974年“英国诉爱尔兰捕鱼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再次运用这一标准来评价国家单边措施在国际法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内的效力,判决爱尔兰运用“延伸50海里以建立捕鱼专属区”的规则对英国不具有可实施性,而没有依照英国最初提出的诉求判决爱尔兰单方面将专属区延伸到50海里的行为违法。[50]这显然是因为国际法院考虑到当时国际法上关于建立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国家已主张建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联合国也正准备通过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明确建立专属经济区的规则。
国际法院上述案件及类似案件[51]的判决表明,在国际法规则缺乏、不明确或者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领域内的国家单边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归入既有规则的适用范围,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非法之列。国际法院承认这类行为在当事国之间具有一定效力,即一国通过单边措施对另一国的行为自由进行限制,依据单边措施的内容,后者有义务采取行动认可或接受其结果。基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学者将具有“可实施性”的单边措施的特征归纳为:(1)有效性(effective),即该单边措施必须被一国有效适用于该措施针对的外国;(2)正当性(legitimacy),即该单边措施是为了公正或国际社会集体利益;(3)诚信(good faith),即实施该单边措施的国家必须诚信的穷尽了其他救济手段。[52]
2.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的可实施性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说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具备一定的可实施性。首先,其直接限制了恐怖主义资助国在受害者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使得国内法院可以对该诉讼进行管辖并依法要求该国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恐怖主义例外”旨在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司法救济并震慑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一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符合公正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最后,尽管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认定“恐怖主义资助国”的行为不可否认具有政治性,被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的国家也无法向任何机构提出申i斥;但对于众多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平民)而言,诉诸国内法院是其唯一可以追究恐怖主义资助国责任的途径。因此,从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角度看,“恐怖主义例外”作为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一项单边措施,对涉嫌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具有国际法上的“可实施性”。当然,正如本杰明·卡多佐法官所言:“国际法(或治理国家间关系的法律),有时候就像普通法一样,是一种模糊不定的存在,很难将它同道德或正义区别开来,直到法院最终的认可才能证实它的法律性质。”[53]对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作为一项习惯法的性质的认定过程也是如此。
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是一国面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诉求所作出的一种非武力回应。当恐怖主义日益危及国际秩序和人身财产安全时,这一豁免例外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乃至效法。201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恐怖行为受害者正义法》,作为该国《国家豁免法》的修正案。该法允许加拿大公民和常住居民中的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加拿大法院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同时,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中的其他受害者,只要能证明该事件与加拿大存在真正实质性的联系,也可以依据该法在加拿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54]2016年3月10日,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组织各国最高法院法官召开“有效审理恐怖主义案件”会议,也表达了联合国对各成员国尽快健全国内司法反恐措施的关注。[55]
五 结语
一国运用国际法规则的能力不仅包括运用既有规则的能力,也包括在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明确的领域创设新规则的能力。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体现了一国通过单边措施使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国内司法救济的努力。依据“恐怖主义例外”,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在其国内法院直接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为其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恐怖主义伤害提供经济上的救济和情感上的慰籍。在国际法层面,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对“恐怖主义资助国”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且很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和效法。鉴于我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反恐挑战,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的同时,也有必要考虑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获得国内法律救济的权利以及实现该权利的法律路径。
【注释】
[1]参见王梦瑶、陈刚:《全球化背景下对反恐怖策略的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33-34页。
[2]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The Global Peace Index 2016 Report, http://economicsandpeace. org/reports/,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3]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cFaddon,7 Cranch 116(1812),paras.137-138.
[4]Letter from Jack B. Tate, Acting Legal Adviser, Department of State, to Philip B. Perlman, Acting Attorney General.(May 19,1952),26 DEP’T ST. BULL.984-985(1952),reprinted in Alfred Dunhill of London, Inc. v. Republic of Cuba,425 U.S.682,714 App.2(1976).
[5]Daveed Gartenstein-Ross, A Critique of the Terrorism Exception to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34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887,894(2002).
[6]Smith v. Socialist People, 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101 F.3d 239,247(2d Cir.1996).
[7]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28 U. S. C.§1605 note (Supp. III1997).
[8]Civil Liability for Acts of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Act,28 U. S. C.§1605 note (Supp. III1997).
[9]Flatow v. Islanmic Republic of Iran,999 F. Supp.1(D. D. C.1998).
[10]例如,在“科容宁诉伊朗案”中,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认为《弗莱托修正案》为个人提供了直接获得救济的权利[Cronin v. Islamic Rep. of Iran,238 F. Supp.2d 222(D. D. C.2002)];但在随后的“斯斯皮欧-普里欧诉伊朗案”中,联邦哥伦比亚上诉法院否定了这一解释,认为《弗莱托修正案》并未提供一项直接起诉外国的个人权利[Cicippio-Puleo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353 F.3d 1024(D. D. Cir.2004)]。
[11]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8,Pub. L.110-181,section 1083(c).
[12]28 U.S. C.§1605 A.
[13]28 U.S. C.§1605 A (a)(1).
[14]28 U.S. C.§1605 A (a)(2).
[15]28 U.S.C.§1605 A (c).
[16]Leibovitch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697 F.3d 561,568(7th Cir.2012).
[17]Flatow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999 F. Supp.1,34(D. D. C.1998).
[18]Ocean Line Holdings Ltd. v. China Nat’ I Chartering Corp.,578 F. Supp.2d 621,624(S. D. N. Y.2008); Intelsat Global Sales & Mktg.,Ltd. v. Community of Yugoslav Posts Telegraphs & Telephones,534 F. Supp.2d 32(D. D. C.2008)[ citing Peninsula Asset Mgmt. v. Hankook Tire Co.,476 F.3d 140,143(2d Cir.2007)].
[19]United Arab Shipping Company v. Eagle Systems, Inc. No. CV408067,2008 WL 4087121(S. D. Ga. Sept.2,2008),at 1.
[20]参见28 U.S. C.§1609。该条款规定,依据美国签署的国际协定,外国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免于扣押和执行。
[21]28 U. S. C.§1605 A (c)(4).
[22]28 U.S. C.§1605(a)(7).
[23]Flatow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999 F. Supp.1,25(D. D. C.1998).
[24]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d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of 2000, Pub. L. No.106-386,§2002,2002(b)(2).
[25]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of 2002. Pub. L.107-297,116 Stat.2337.
[26]28 U.S. C.§1610(a)(b).
[27]28 U. S. C.§1605 A (g)(1).
[28]Iran Threat Reduction and Syria Human Rights Act of 2012,22 U. S. C.§8772.
[29]Bank Markazi v. Peterson,136 S. Ct.1310(2016),p.2(b).
[30]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Iran institutes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gard to a dispute concerning alleged violation of the 1955 Treaty of Amity, http://www.icj - cij.org/docket/files/164/19032.pdf,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31]目前该名单上的国家包括苏丹、伊朗和叙利亚,曾经在名单上现已经被移去的国家则有伊拉克、也门、利比亚、朝鲜和古巴。参见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http://www.state.gov/j/ct/list/cl4151.htm; Molora Vadnais, The Terrorism Exception to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orward Leaning Legislation or Just Bad Law?,5 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Foreign Affairs 199,228(2000)。
[32]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 S.2040,114th Congress (2015-2016),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4th-congress/senate-bill/2040/text,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33]该法通过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受害者及其家属起诉的目标国家。沙特阿拉伯曾极力反对该法,声称在美国法院冻结其财产之前将出售其持有的7500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及其他资产。奥巴马总统亦反对此项立法,认为该法案严重损害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盟国关系,并使美国境外工作人员同样遭受被起诉的风险。美国国会最终以绝对多数票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该项立法行使的否决权。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的如下发言反映了支持该项立法的议员们的态度推翻总统的否决权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事,但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9.11受害者家属应当被允许追求正义,即使该项追求引起一些外交不适。”参见Bill Allowing 9/11 Victims to Sue Saudi Arabia Becomes Law, http://www.newsweek.com/September -11- victims - bill - becomes - law -504010? amp=1,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34]Ilana Arnowitz Drescher, Seeking Justice for American Forgotten Victims: Reforming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Terrorism Exception,15 NYU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791,816(2012).
[35]Molora Vadnais, The Terrorism Exception to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orward Leaning Legislation or Just Bad Law?5 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199,225-226(2000).
[36]参见汪自勇:《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救济与主权豁免——美国公民针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诉讼评介》,《武大国际法评论》2006年第2期,第386页。
[37]28 U. S.C.§1605(g)(1)(A).
[38]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 Sec.5. S.2040,114th Congress (2015-2016).
[39]《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法》通过后次日,美国国会两院议长就公开表示愿意考虑修改该法。参见Day After Rejecting Veto, Congressional Leaders Concerned About 9/11 Law,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ongress-saudi-arabia-bill-doubts_us_57ed6491e4b024a52d2dbl3d,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40]Judgment No.238, Italian Constitution Court (2014).
[41]Verlinden B. V. v. Central Bank of Nigeria,103 S. Ct.1962,1967(1983).
[42]Martha Finnemore &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1998), p.887.
[43]这些协议包括《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行为公约》(1963)、《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1970)及其2010年《补充议定书》、《制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服务机场的非法暴力行为议定书》(1971)、《制止和惩罚对国际保护人员犯罪公约》(1973)、《国际反劫持人质公约》(1979)、《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0)、《制止在民用机场非法暴力行为公约》(1988)、《制止危及航海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制止危及位于大陆架上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协定书》(1988)、《可塑炸药公约》(1991)、《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公约》(1997)、《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1999)、《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2005);《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2005)、《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年议定书》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之2005年议定书》。上述公约或议定书的内容可以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zh/terrorism/instruments,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44]《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A/RES/49/60),1994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页。
[45]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第1页。
[46]安全理事会第2249(2015)号决议,第1页。
[47]安全理事会第2249(2015)号决议,第2页。
[48]《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5条规定的四类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恐怖主义罪尚未纳入其中。卡塞斯将恐怖主义罪列为一种国际罪行,认为它可能构成战争罪(如果恐怖主义行为是在武装冲突中实施的),也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如果满足危害人类罪的要求),还可能构成其他独立罪行。参见[意]安东尼奥·卡塞斯著:《国际法》,蔡从燕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49]Fisheries Case, Judgment of December 18th ,1951: I. C. J. Report 1951, p.116(26).
[50]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 Iceland),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4, p.3(139).
[51]国际法院运用了“可实施”、“不可实施”或类似概念的判决还有:The Right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Morocco (1952)'Temple of Preah Vihear (1962)'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1980)'Frontier Dispute (1986)以及East Timor (1995)。
[52]Shinya Murase, Unilateral Measures and Opposability,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n Transboundary Issues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Tokyo,2011, p.241; J. G. Starke, The Concept of Oppos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1968—1969,pp.1-4.
[53]New Jersey v. Delaware,291 U. S.361,383(1934).
[54]Justice for Victims of Terrorism Act.依据该法起诉的外国必须是被加拿大政府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的国家。2012年以来名单上的国家为伊朗和叙利亚。参见Order Establishing a List of Foreign State Supporters of Terrorism ,http://www.gazette.gc.ca/rppr/p2/2012/2012-09-26/html/sordors170-eng.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55]参见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新闻网,Closing Statement by ASG and Ed Jean-Paul Laborde at CTC Briefing on “Upholding Justice” with Supreme Court Justices,10 March 2016, http://www.un.org/en/sc/ctc/news/2016-03-16_JPLabor-de_UpholdingJustice.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12-18]。
【作者简介】王蕾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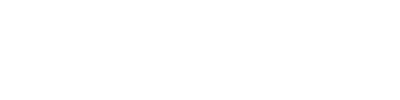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