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三平 苏建召
案情简介
2013年9月,韩某与河南金基租车公司(以下简称“金基公司”)签订了投资托管理财合同,约定韩某出资10万元购车交由该公司管理。合同期限三年,公司每月向韩某支付投资收益1400元,到期后韩某可选择要车或返还一定比例的现金。金基公司将车辆租给张某,约定张某支付14万元租车押金后,每月向金基公司交纳租金2000元。2015年金基公司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韩某无法向金基公司追回租出车辆。曾为金基公司员工的陈某看到了“商机”,便利用自己掌握的投资客户信息,与韩某约定由韩某出具委托书,自己组织民间“收车队”将其车辆“合法收回”,由韩某支付收车费用7.3万元。2016年1月10日,陈某伙同林某、杨某等人通过GPS定位和私配钥匙,将张某承租的车辆收回并交付车主韩某。截至案发前,陈某等人利用相同手段先后在河南省内分布有金基租车网点的城市作案近20起,获利近290万元。
分歧意见
该案中,围绕可通过民法调整的违法行为能否评价为刑事犯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可通过民法调整的违法行为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金基公司倒闭后,车辆所有权人索要车辆无门,不得已求助民间“收车队”讨回自家车辆,属于私力救济行为。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有在不得已情形下才能适用。车主韩某及陈某等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承租人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就该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韩某委托陈某等人未告知承租人即私自收车,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但收车后物归原主,既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韩某及陈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侵财型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承租人依租赁合同取得了对车辆的占有权,该占有属于侵财型犯罪所保护的法益。车主及陈某等人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可通过民法调整的违法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刑事犯罪,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对韩某、陈某的刑事规制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旨;关于该案的定性,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韩某、陈某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可通过民法调整的违法行为能否评价为刑事犯罪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刑法的发动不应以所有的违法行为为对象,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制违法行为时,才能使用刑法,即刑法只对当罚的行为进行评价和处罚,而不应随意超越界限。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不得将可通过民法调整的违法行为评价为刑事犯罪。实践中,侵权行为的范围较为宽泛,多数属于民事、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少数属于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行政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的范围。例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在民法上属于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行为,但不能据此排除这类行为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可能。同样,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侵财型犯罪。例如,一房多卖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能够通过民法调整的侵权行为,不排除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至于能否评价为刑事犯罪,应当依照罪刑法定原则,结合刑法规范加以具体考察。
就该案而言,车主韩某与承租人之间并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承租人依合同向汽车租赁公司交纳了高额押金,每年还要交纳数千元的租赁费用,该租赁合同受法律保护。陈某等人采取秘密手段“收车”完全出乎承租人的意料。陈某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暴利”,车主韩某为降低救济成本寻求非法的“私力救济”,使第三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在给承租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汽车租赁市场的交易秩序,使承租人丧失了正常的交易安全感。若仅采取民事法律规范加以调整,无法从根本上抑制这种低成本违法行为的蔓延。该违法“收车”行为完全超越了私力救济的法律底线,不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该行为适用刑法加以规范乃不得已而为之,与刑法的谦抑性并不矛盾。
二、占有权能是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之一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财产罪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整体,但该理论无法有效解决所有权权能与权利整体存在分离的问题。当前,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财产罪侵害的客体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整体,即包括财产所有权及其每项独立的权能,以及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恢复的部分非法占有。占有是指对人与物事实上的控制与支配,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除所有权人的自主占有之外,基于承包、土地使用、质押、留置等,会产生物权意义上的他主占有;基于保管合同、租赁合同、承担合同,也会产生债权意义上的他主占有等。当然,还有一些是基于违法犯罪所得产生的非法占有。由于占有权能在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基础性地位,确立了占有这一事实成为财产罪保护的重要法益。
我国物权法设立了占有保护制度,规定占有人均可基于管领物的事实而成立占有。占有一旦存在即受保护,任何人不得以私力强行改变占有现状。因此,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核心,是有效地保护占有合法性。否则,现存的占有秩序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对占有的保护当然也是全面的:既保护所有的合法占有,也保护部分非法占有。质言之,占有不能对抗所有权人,若所有权人实施盗窃等非法行为取回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产,则不能评价为刑事犯罪,这是刑法保护的例外部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毒品、假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抢劫赌资,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由此可见,刑法对占有的全面保护理念,早已被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所认可。
该案中,车主韩某对自己名下的车辆享有财产所有权,但韩某将车辆交由汽车租赁公司托管,再由汽车租赁公司租赁给承租人后,其占有权能便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通过汽车租赁公司移转至承租人。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合法占有了车辆,该占有属于债权意义上的他主合法占有。刑法对该占有是予以保护的,承租人完全可依该占有对抗财产所有人。车主韩某与汽车租赁公司之间是一种投资理财合同关系,与承租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汽车租赁公司违约,车主韩某应当起诉该公司,但无理由向承租人主张权利。
三、行为人秘密收回车辆交回车主本质是对赃物的事后处分
由于车主委托“合法收车”模式披上了形式合法的外衣,该案具有较大的欺骗性。表面上看,陈某等人将车辆“收回”后交给了车主,似乎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质上,这是陈某等人盗窃财物后对赃物的一种事后处分行为。因为,陈某等人并没有采取合法手段收车,而是秘密窃取特定第三人(承租人)合法占有的车辆,该行为与一般盗窃没有本质区别,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车主韩某虽然委托陈某等人“合法收回”,但实质上是与陈某等人共谋盗窃。因为韩某明知自己无权向承租人主张权利,承租人已向汽车租赁公司缴纳了高于汽车原值的高额押金,若不向承租人支付相应对价,根本无法从承租人手中讨回租赁物。而陈某等人要“平和”地完成这一“委托”任务,只有实施盗窃。韩某依事前约定,事后向陈某等人支付1.3万元“收车费”,就是向陈某等人支付违法犯罪的“风险费”(实质是分赃)。因此,基于非法占有故意这一事前通谋,车主韩某与“收车队”陈某等人成立盗窃罪的共犯。
作者简介:屈三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苏建召,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检察院。
来源:《人民检察》2016年第20期(总第72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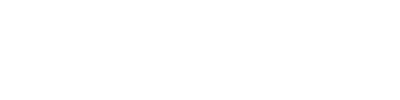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