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与侦探──谈公案小说中的侦探作品
发布时间:2017-09-20 信息来源:太琨律品牌律师 浏览次数:1306
欧美侦探小说译著在中国风行之初,小说家吴趼人曾奋起抗争。他选辑了一部《中国侦探案》,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侦探完全比欧美的侦探高明。但吴趼人的努力在当时未能引起国人的重视。直待欧人高罗佩以中国古代的侦探做主角,写出多卷的《狄仁杰故事集》,饮誉西方30载后又返销到中国来,这才引发国人重视起中国古代的侦探。
欧美侦探小说的兴起至今才一个半世纪。这是因为近现代刑事侦查制度在欧美建立较晚,至今不到两个世纪。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侦探作品和欧美侦探小说不能用同一种概念来衡量。在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董仲舒说,“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罪。”(《汉书·董仲舒传》)“督奸”,恐怕已含有刑事侦查的意味。《周礼·秋官》记载周代有司稽、司隶、禁暴民、司虣等职能类似于现代治安、刑事警察的官吏,也许不可凭信,但《国语·周语》所记的周厉王时“监谤”的卫巫,则明显负有警巡、侦查的任务。秦汉以降,郡(州)、县设有贼曹,官吏专职捕盗。县尉的职掌也是维护治安,缉捕盗贼。城区县乡中又有游缴,专门巡察贼盗,维护治安。唐宋时,州郡又设司法、司理参军,负责审理刑狱,督察盗贼。《水浒传》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后,负责追缉的是济州府的缉捕观察何涛。这说明,宋以后,州中有专职的侦缉官吏。辽、金、元时,都城设警巡院,明时称五城兵马指挥司,清代称作九门提督,职掌都是警巡京师,缉捕盗贼,维护治安。中国古代的刑侦制度还有一个特色,即地方各级行政长官负有侦审刑案的责任。所以,明清白话公案小说的侦探主角——包拯、施士伦、狄仁杰等人,都是地方行政长官。
严密的刑事侦查制度,促成了刑事侦查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刑侦科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果辉煌。专论现场勘查、痕迹检验等的规章要求、方法步骤的秦代的《封诊 式》,已全面总结前人刑侦技术经验;在法医学方面有巨大成就的宋人的《洗冤集录》,更是代表中国古代刑侦科技的典型性著作。
悠久的“侦探”历史,高度发展的刑侦科技,是侦探小说产生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中国早期的公案小说中就有侦探作品。早期侦探作品常以刑案侦查的技术手段为主要描写内容,如《搜神记》中的《严遵》,《朝野佥载》中的《蒋恒》、《王璥》、《张族》、《张楚金》等。侦查推理也为小说家所注重,《朝野佥载·董行成》、《纪闻·苏无名》、《玉堂闲话·杀妻者》都成功地描写了侦查推理。五代时和凝编《疑狱集》,侦探作品开始被收辑。宋代《太平广记》“清察”类二卷辑入的公案小说大部分是侦探作品。至郑克编《折狱龟鉴》,收辑的侦探作品更多。元明清时期的文言公案小说中,侦探作品始终占很大比例。明清人增补《疑狱集》、《折狱龟鉴》等,增入的作品不少是侦探作品。冯梦龙《智囊补·察智部》辑入的不少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公案作品,以及《详刑古鉴》、《不用刑审判书》等辑入的大量作品,都是写侦探故事的。晚清吴趼人编的《中国侦探案》则是以“侦探”命名的名符其实的侦探小说集。
初期的白话公案小说,侦探性质的作品较少见。元代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有些侦探意味。《水浒传》中写何涛兄弟探明黄泥冈上的作案者和黄文炳识破吴用伪造的蔡京书信,也可作侦探故事阅读。不过,白话侦探作品的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三言”中的《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滕大尹鬼断家私》、《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二拍”中的《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以及《详刑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等公案小说集中的不少作品,是单篇白话侦探作品。《龙图公案》等则是类似于爱伦·坡“杜宾故事”、勒白朗《亚森罗宾探案集》的系列侦探作品集。而《施公案》和《三侠五义》的前数十回以及《狄梁公全传》等,无疑都是长篇侦探作品。
文言公案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是为官作宰的文人。他们有侦审刑事案件的经验,懂得刑事侦查技术。他们有吸取前人侦审技术经验的需要,也有为后人提供侦审技术经验的责任。他们一般以历史上或现实中成功的侦破案例为蓝本,着力于叙写各类刑侦官吏的侦破才能、经验和技术。其写作态度一般求实。所以,文言侦探作品适宜于编入《折狱龟鉴》一类书中。白话公案小说的作者则较少刑案侦破的技术经验。《水浒传》写及案件侦缉完全是嘲讽批判性的。“三言”、“二拍”中的侦探作品,主题在“警世”、“醒世”方面,并非作“折狱”之“龟鉴”。明末的书商们搜集侦破案例改写成白话后编集出版,目的更在于以新奇刺激的内容赢得较佳的经济效益。《龙图公案》以及清代长篇侦探小说的创作思想要复杂一些,“折狱龟鉴”的功用也不能忽视。但是,这些作品的给刑案侦破提供借鉴作用,主要不在于刑侦技术经验方面,而在于执法的精神,即上承《尚书》“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的执法思想,颂扬忠君爱民、秉公明断的清官。“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明安在哉!”(李西桥《龙图公案序》)秉持公心是首要的,侦审的技术经验则在其次。《龙图公案》等除了这样的创作思想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其牟利的创作目的。刑案侦破的故事生动引人,说书人中有专说这类故事的。《三侠五义》原稿《龙图耳录》即是据石玉昆说书的记录整理成的作品。
欧美近现代侦探小说的一大特色是以欧美刑侦科技为叙写内容,大量描述侦探们运用法医学、毒物学、指纹学、心理学以及侦查推理等知识技能侦破案件的故事。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不少侦探作品也有类似之处,是以中国古代“侦探”的刑侦手段的高明、智慧为描写重点的。《搜神记·严遵》便是这类作品的早期代表。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枉。”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搜神记·严遵》)
严遵侦案原见于《益都耆旧传》,《搜神记》增加了一些情节,并有意写得扑朔迷离,带点神鬼气息。其实,揭去其神秘面纱,就可发现,这篇小说为了塑造严遵这一侦探形象,糅合性地叙写了中国古代的几项刑侦技术。
其一,严遵听到女子哭祭死去的丈夫而“声不哀”,即疑情况有异。这是继承了前人的刑事侦破经验。春秋时就有子产“听哭辨奸”的故事。子产当时还说出一番社会心理学的依据:“夫人之于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非子·难三》)子产的故事后来被小说家写入了《独异志》。在唐宋而后的公案小说中,也常能见到能“听哭辨奸”的侦探形象。
其二,严遵与尸体说话,并说“死人自道不烧死”。这看上去很熟神秘。实际上,他是做尸体检验。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产生于先秦。尸检技术在秦代的《封诊式》中已有详细具体的描述。严遵不仅懂得尸检,而且根据尸体口腔的情状即判断出是死后焚尸。这种判断是有他人的侦查实验做依据的。三国时东吴句章令张举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件。为了鉴定死者是烧死还是死后焚尸,张举“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而积薪烧之。活者口中有灰,杀者口中无灰。因验尸口,果无灰也”,于是断定是死后焚尸。(见《疑狱集》)当然,这里有个矛盾。严遵是汉代人,不可能借鉴三国时人张举的经验。但是,这验尸的情节正是《搜神记》所增加。所以,这应是晋代的小说家将三国时人的侦查技术移植到了汉代侦探的身上。后代的公案小说也很重视用这一侦探技术来刻画侦探形象。《施公案》第七十八回,张氏谋杀了亲夫孟文科,诡称“男人吃醉,不幸被火烧死”。施士伦即令烧羊验尸,因而查明了案情。
其三,严遵令人守尸,是要求进一步查验。他们也终于发现了致死原因——头顶的铁钉。铁钉贯顶杀人,在当时应属技术性犯罪。发窠中间的细铁钉是不易查出的。技术性犯罪是刑侦技术发展后出现的一种反侦查行为。铁钉贯顶杀人一类的手段在唐宋时期常有效仿者,公案小说中时有描写。宋时写张咏侦审“双钉案”故事的小说(见《折狱龟鉴》)便是其中的典型作品。明代的《龙图公案》也写入了“双钉案”故事(《白塔巷》)。
“福尔摩斯探案”的《巴克斯维尔的猎犬》中曾有一封用报纸文字剪贴成的匿名信。这是作者通过笔迹学运用于刑事侦查的文学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样的故事情节和描写手段,在中国唐代的一篇公案小说中有过绘声绘色的表现。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佥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朝野佥载·张楚金》)
“割字合文”伪造谋反信以诬告他人,案犯如此作案,显然是在笔迹上大做手脚。检验笔迹以破案,最早见于三国时魏郡太守国渊侦破诽谤信案。那是一封诽谤曹操的匿名信。国渊根据信中大量引用张衡《二京赋》词句的特点,派人以求师为名找到了一位深谙《二京赋》的学者,然后设计套取其笔墨,再与诽谤信比对笔迹,从而成功破案。这些说明,无论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抑或刑侦技术,都注意到了笔迹检验和语言风格鉴别。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所描写的笔迹检验技术与欧美近代的笔迹检验技术不尽相同。柯南道尔笔下的拼贴信,一看即知是拼贴而成。侦探的才智主要发挥在查明拼贴所用文字的来源、拼贴时所用的工具等。中国古代的侦探作品则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的智慧。
侦查推理是欧美侦探小说最擅长的描写内容,所以,侦探小说往往又被称做推理小说。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也很重视侦查推理。《朝野佥载·董行成》写董行成识破盗驴贼,就是依据推理。《玉堂闲话·杀妻者》写府从事分析“杀妻案”:“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身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面弃首?其理甚明。”这正是侦查推理。《纪闻·苏无名》叙写侦查推理更为典型。太平公主的珠宝被盗,苏无名奉武则天之命侦查。破案获赃后,他为武则天介绍全案:“当臣到都之日是,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此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这精到周密的分析推理,比之欧美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毫不逊色。
白话公案小说也重视刑侦技术经验的叙写。《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写指认案犯,查找左腰间“大如铜钱”的疮痕,便属于法医学的活体检验。《龙图公案》中,《木印》写印记核对,《石碑》写布匹认定,都是物证检验。《三侠五义》写包公侦审杀僧案,进行了对六指手印的比对;写皮熊毕氏通奸杀人案,也对珊瑚扇坠作了物证鉴定。《施公案》写“姜酒烂肺”,《三侠五义》写“尸龟毒”,都涉及毒物学的知识和经验。侦查推理也常见于白话公案小说作品中。《龙图公案·房门谁开》中审明公公与儿媳的奸情,即用推理方法。《三侠五义》第五回包公排除沈清作案可能,也用推理方法。《狄梁公全传》写狄仁杰侦审案件,侦查推理运用得更为普遍。
不过,白话公案小说的写作一般是改编移植文言公案小说的刑案侦破内容。归结于包公、施公、狄公等名下的一个个侦破故事,大都是从前人的文言侦探小说作品中搜辑而来。因此,塑造不同“侦探”形象的不同的侦探小说常会出现雷同的侦探故事和侦查手段。只是后期的作品较前期的作品,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更感人一些罢了。所以,白话公案小说写刑案侦破故事,刻画侦探形象,一般是注重于将前人记写的疑难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以疑案侦破的高难度表现侦探的高水平。《三侠五义》第九、十、十一回构设的“金箱”、“猪头”案,就是以前人故事为基础,进一步综合化、复杂化的典型例子。《狄梁公全传》中的“奇案”,更是糅合前代许多疑难案情而制造的产品。至于刑侦技术手段的创新,在白话公案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当然,除了制造“奇案”,白话公案小说塑造侦探形象还有独到的手法。这就是,一、以鬼神阴助神化侦探形象;二、以侠士辅佐强化侦探威力。
白话公案小说一般以忠君爱民、秉公明断的执法官为主人公。包公、施公、狄公都是这类人物。李西桥认为,只有“公”才能“明”,侦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执法的道德水准的高低。这实际上正是白话公案小说塑造侦探形象的主导思想。《龙图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狄梁公全传》等都突出描写主人公的忠君爱民、秉公执法。许多疑难案件在这样的执法精神面前,往往都化难为易,甚至有时不侦自破。这里边最具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便是鬼神的阴助。《龙图公案》中的一百个案件,大多数是在阴风、梦兆等的助佑下侦破的。《施公案》中的第一件大案——“九黄七珠”案——也是凭梦兆而破获。其后的许多疑难案件的侦破,也都得到鬼神助佑。《三侠五义》也常写到鬼神助包公侦审案件。有时包公为了查明案情,还通过游仙枕直达阎罗殿。《狄梁公全传》产生于“西风猛吹”的清末,内容已受欧美侦探小说译著的影响,但狄公审案,时常还少不了梦中兆示、阴风引路之类。
白话公案小说常写主人公“微服私访”。这有点象欧美小说中的侦探。但在中国古代,文人法官做秘密侦查很有危险性。爱扮成乞丐的施士伦就曾被案犯识破,差点儿被吊打丧命。既要秘密查案,又能让“大侦探”过于冒险,于是,白话公案小说作者便请来武侠帮忙。先是《施公案》中请入黄天霸。到了《三侠五义》中,王、马、张、赵都投到包公门下,更有御猫、五鼠等侠客,都常助包公秘密探查案情。而《狄梁公全传》中众多奇案的探明,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马荣、乔泰、陶干的高强手段。正是武侠们的辅佐,强化了包公等“大侦探”的威力。
欧美侦探小说也常写到警官们将私家侦探的功绩据为己有,但其笔调是嘲讽性的。在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中,侠士们的侦查成果归功于其“恩主”,则完全“天经地义”。并且,“恩主”们会因此而更闪辉光,更值得颂赞。从这里,我们既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官吏、幕僚制度,也可以进一步窥见中国古代对于权威的文化心态,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这与鬼神阴助一样,表现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特色。
(刊于《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2期)
来源:东方法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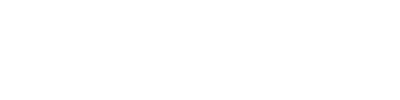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