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勤
【摘要】 对非法拘禁导致被害人自杀死亡的案件,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存在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重要原因说、客观归责说等多种观点,导致对同类案件要么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要么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存在将因果关系、结果加重犯和实质数罪混为一谈等问题。一方面,应当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肯定因果关系并不表明对行为人必须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论处。因为在非法拘禁这类封闭的作案环境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负有保护义务,有义务防止被害人自杀或他杀事件的发生,未履行这种保护义务的,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视罪过不同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应与非法拘禁罪(基本犯)数罪并罚。
【关键词】 非法拘禁;自杀;致人死亡;故意杀人;不作为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法定刑则为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1]近年来,因追索合法或非法债务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日益增多,其中不乏被害人因不堪忍受拘禁或折磨而自杀身亡的例子,对于此类案件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从而对被告人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在理论上及实践中均存在很大争议,而这两种法定刑相差7年以上的结果,对被告人权益的影响是巨大的。
例如,在“非法拘禁致被害人景某自杀”一案中,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非法拘禁致被害人死亡,法院则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过身体伤害与精神折磨,故被告人主观上对被害人的跳楼无法预见,客观上其行为不具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性,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以非法拘禁罪的基本犯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以下简称【案例1】])。[2]而在“郭某非法拘禁致被害人吴某自杀”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郭某等人为索取债务共同非法拘禁他人,其非法拘禁是导致被害人坠楼死亡的重要原因,故以非法拘禁罪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下简称【案例2】)。[3]
可见,【案例1】与【案例2】的案情几乎完全相同,但量刑相差8年以上!两个案例的判案理由之一都是因果关系,却对同样的案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同案不同判并且量刑差异巨大的现象,既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又必然有一案严重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这种现象表明,仍有必要对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案件的定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对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之定性的不同观点评析
对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死亡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全面肯定说
此说认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指因实施非法拘禁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包括被害人自杀死亡等情形。[4]最高人民检察院1986年3月24日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一些问题的说明》(该司法解释已被废止)中指出:“……该条所说的‘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指在非法拘禁过程中,由于暴力摧残或其他虐待,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以及被害人在非法拘禁期间自杀的。非法拘禁解除后被害人自杀的,要根据具体情节分析认定,一般不宜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可见,该司法解释明确将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规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刑法》第240条第1款将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亲属死亡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升格情节,也是将致使被拐卖者的亲属自杀死亡作为致人死亡的一种情形,因为可以预见,亲属死亡基本上都是自杀死亡,至少不排除自杀死亡。
可见,在此说看来,被害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自杀身亡的,均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这种观点认识到非法拘禁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充分考虑了被害人一方的利益,是正确的,但是,仍不尽妥当:
第一,不顾具体案情一概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从而对被告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被告人可能过于苛刻。例如,在“张某非法拘禁案致张X自杀”一案中,被告人张某以本班小学生张X未完成作业为由,放学后将张X反锁在教室内令其补做作业,并将门锁钥匙交给值日学生刘某后离去。一小时后,有人发现张X已在教室内自缢身亡。对此案例,法院认为,被告人因被害人未做完作业而采取非法手段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下简称【案例3】)。[5]此案中,非法拘禁行为持续时间不足一小时,且拘禁目的只是让被害人补做作业,其社会危害性并不算大,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是过于苛刻的。
第二,该观点未深入考虑被害人自杀的原因等诸多问题。例如,被害人自杀是由非法拘禁所致,还是被害人本来就打算按计划自杀?这不能不考虑因果关系问题。又如,“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还是法律拟制?其与同款后段“使用暴力致人死亡”之间是何关系,换言之,对于非法拘禁手段以外的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再如,虽然不否认被告人要对被害人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能否仅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责,而不是“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之结果加重犯罪责,等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第三,按这种观点未必能解决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的定性问题。因为所谓过失,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因为发生了危害结果而对行为人目的行为的一种评价,所谓“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中的“应当”,即表明事实上没有预见,但被评价为“应当”预见。因此,如果倾向于认为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就会评价为“应当预见”,如同【案例3】中那样。在【案例3】中,被告人不过是为了让学生完成作业而将学生锁在教室内,拘禁行为持续时间短暂并且没有殴打、胁迫等情节,却被评价为对被害人自杀身亡的结果应当预见。反之,如果认为被告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则会评价为被告人“不应当预见”,如同【案例1】中那样。在该案例中,被害人先被押送至朋友家借钱还债未果,继而被继续押送看管,其时已近深夜,何时能被放回、会受到何等摧残还不确定,若与【案例3】相比,无疑更应被评价为“应当预见”,却被评价为意外事件。尽管可以从理论上提出一些认定“应当预见”的标准,但实际上,目前学术界尚无一个大家公认并一致遵循的标准,更无法替代个案分析,因此就同样的案情,不同的人完全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由于认定“过失”的标准过于含糊,根据此说仍然无法解决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
(二)全面否定说
此说认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是指非法拘禁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死亡,因而不包括被害人自杀情形。认为死亡结果与非法拘禁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直接性要件),必须是基本行为具有造成加重结果的高度危险并且直接造成了加重结果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就致死类型的结果加重犯而言,要以致命性的实现的有无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是后行为或其他因素导致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缺乏直接性关联的,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基本行为之时或之后,被害人自杀自残或因自身过失等造成严重结果的,因缺乏直接性要件,不宜认定为结果加重犯。[6]
可见,在此说看来,因被害人自杀等造成死亡的,由于缺乏直接性要件,不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此说有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借用结果加重犯理论中的直接性要件理论来一概否定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未必合理,忽略了被害人自杀发生于被非法拘禁这一特定环境。在上述案例中,被害人之所以产生自杀意图,是因为被非法拘禁,非法拘禁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具有条件关系。又如,假设被告人眼见被害人上吊自杀而不制止,甚至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却仅让其承担非法拘禁基本犯的罪责,对其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很不合理的,对被害人明显不公平。
其次,适用此说可能导致放纵杀人、鼓励杀人的后果。因为在非法拘禁这类封闭的作案环境中,被害人到底是自愿自杀还是被胁迫而自杀,由于被害人已死而现场又无目击证人,往往难以查证。甚至即使被害人并非自杀,而是被被告人杀害,比如从楼上推至楼下、从岸上推至河中等,由于难以查证而不得不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这无疑会放纵试图利用这一理论漏洞的犯罪分子,客观上起到放纵杀人、鼓励杀人的后果。
再次,适用直接性要件理论会过分缩小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例如,被告人在二楼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奸淫,该妇女为了避免受害仓皇逃跑,误从窗台上坠落至楼下摔死;被告人在飞速行驶的汽车中对被害人施加暴力,被害人因不堪忍受而从汽车上跳下摔死,对此二案,德国法院曾经以缺乏直接性要件为由,否定强奸致死和伤害致死的成立。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德国法院这样做无异于鼓励被告人犯罪,却让被害人承担忍受犯罪人侵害的义务,这对被害人显然不公平,是人为地缩小了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7]
最后,此说与论者所主张的因果关系理论相矛盾。其一方面主张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首先适用“合法则的因果关系”,但是当难以适用时则适用“条件关系”,一方面又主张在结果加重犯中应适用“直接的原因说”,但是对其理由却无法说明。所谓“直接的原因说”,也无非是被其批判的早已过时的原因说。[8]
此外,另有学者从主客观归责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其认为,在被害人自杀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基本行为并未创设被害人自杀身亡的风险,更未实现这个风险,所以死亡结果不得归责于行为人,换言之,虽然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自杀身亡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但是在客观归责上,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在主观归责方面,只有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预见可能性或者说至少存在过失时,才可以对死亡结果进行主观归责,但是在被害人自杀身亡的场合,行为人对此缺乏预见可能性,不存在过失,更不存在故意。[9]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可能与客观实际不符,比如在被害人因不堪忍受非法拘禁过程中的殴打或侮辱而屡次流露出要自杀的语言或行动时,无法认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自杀身亡缺乏预见可能性,比如见被害人撞墙或跳楼自杀而不制止、不抢救,就不可能断定拘禁者对被害人的自杀无法预见;断言行为人的行为并未创设被害人自杀身亡的风险,也过于简单化,比如将被害人拘禁在极端封闭的场所并经常殴打、侮辱、断水、断粮致使被害人身体极端虚弱而难以忍受时,完全可以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创设了被害人自杀身亡的高度危险,被害人实际自杀则是这种风险在结果中实现。
(三)部分肯定说
与全面肯定说和全面否定说不同,部分肯定说主张有条件地承认被害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自杀身亡的案件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其中又有几种观点。
1.主要原因说。此说认为,对于被害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死亡的,能否认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取决于非法拘禁是不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是,就应当认定有因果关系,反之,则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一般来讲,在以下几种场合能认定非法拘禁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过失长时间捆绑被害人致被害人血液不流畅而死亡,因过失使被监禁的被害人因饿、热、冻、病等死亡,被害人不堪忍受拘禁而自杀(如自缢、跳楼、跳水等),被害人不堪忍受拘禁在逃离监禁过程中不慎死亡(如从楼上掉下)等。不包括在非法监禁过程中,被害人因心脏病突发病逝、被害人因还债无望而自杀、被害人因抽烟不慎引起火灾导致自己被烧死等。[10]
2.必然、直接原因说。此说认为,作为一种结果加重犯,非法拘禁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限于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致人死亡是指非法拘禁行为本身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如因长时间捆绑而使被害人身体生命体征消失而死亡,因过失致使被拘禁人因冻、饿、病而死亡,被拘禁人因不堪忍受而自缢或跳楼死亡等。不包括非法拘禁行为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如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被拘禁人突发心脏病衰竭而死亡、被拘禁人为脱逃在跳楼时摔死、被拘禁人抽烟生火引发火灾烧死他人等,这里死亡后果的出现与非法拘禁行为并无一般意义上的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应当理解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暴力摧残或其他虐待,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或经抢救无效死亡,以及被害人在非法拘禁期间因不堪侮辱、打骂而自杀死亡。[11]
可见,以上两种观点尽管说法不同,前者提主要原因,后者提必然、直接原因,但结论却大同小异,并且都认为应将被害人因不堪忍受拘禁、侮辱、打骂而自杀身亡等情形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第一,两种观点均想从导致结果发生的众多原因中挑选出一个原因作为刑法上的原因,这属于刑法学界早已过时的原因说。[12]因为要从对结果起作用的诸多条件中挑选一个条件作为原因,不仅极为困难和不现实,而且会导致因果关系认定的随意性,况且结果的发生,并非总是依赖于一个单纯的条件,在不少情况下应当承认复数条件竞合为共同原因。[13]
第二,何谓主要原因、必然、直接原因,其认定标准相当模糊,难免导致恣意认定。例如,同样是主张直接的因果关系,全面否定说认为被害人自杀身亡与非法拘禁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必然、直接原因说则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样是考察非法拘禁行为能否导致被害人死亡,全面否定说认为非法拘禁本身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部分肯定说则认为非法拘禁本身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同样是为了脱逃而在跳楼时摔死,必然、直接原因说认为不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主要原因说认为属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第三,在主要原因说看来,在被害人因还债无望而自杀时,非法拘禁不是主要原因,而在被害人因不堪忍受而自缢或跳楼死亡时,非法拘禁又是主要原因。这有自相矛盾之嫌,试想,被害人为什么会因为感觉还债无望就自杀?不正是因为害怕因无钱还债而被无期限非法拘禁下去、害怕被非法拘禁期间受到非人折磨,从而不堪忍受这种非法拘禁而起意自杀吗?
而依必然、直接原因说,同样是因为不堪忍受,如果被害人直接自杀,就属于有必然、直接的联系,如果被害人为了脱逃而在跳楼时摔死,就不具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仅从死亡与非法拘禁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则跳楼时不慎摔死与通过跳楼自杀而死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非法拘禁所引起的跳楼,而跳楼几乎必然导致摔死。
第四,同全面否定说一样,上述两种观点均将归因与归责混为一谈,以应否归责来决定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倒果为因之嫌。即,由于认为应当归责(这是“果”)而认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来的“因”,有该“因”才有应当归责之“果”)。
第五,这两种观点不具有可操作性。其一,通常情况下,非法拘禁案件中都存在胁迫或殴打情节,否则,被害人不会害怕,行为人不可能达到非法拘禁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使真的没有明显的胁迫或殴打情节,将被害人一直拘禁下去,本身也是一种精神折磨。依此,【案例1】中以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等对被害人实施了身体伤害和精神折磨为由,否认非法拘禁与被害人自杀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是错误的。其二,两种观点都提倡“不堪忍受”标准,但是,该标准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由于被害人已死,如何证明他是因不堪忍受殴打、侮辱、胁迫或非法拘禁而自杀?即使被害人没死,也无法证明他是能够忍受还是不堪忍受。
3.客观归责说。此说认为,应当根据客观归责理论来认定是否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认为依据客观归责原理,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要求非法拘禁行为本身具有致人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包括三种情形:一是非法拘禁行为本身包含足以致使一般人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二是非法拘禁行为虽然不具有足以使一般人重伤、死亡的风险,但是结合被害人的自身素质(如被害人患有严重疾病、精神异常等)而特别地具有了致人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三是非法拘禁行为虽然没有一般的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被容许的风险,但非法拘禁行为实施的环境蕴含了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被容许的风险。
具体来说,下列情况应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1)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所实施的排除被害人反抗的行为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2)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有身心发育不全的被害人自伤、自杀;[14](3)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被害人因为身体上的危险(饥饿、疾病等)的存在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导致重伤、死亡;[15](4)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被害人为了逃脱受拘禁状态不慎致自己重伤、死亡。[16]
相似观点认为,在肯定条件关系之后,还要筛选刑法上可资归责的原因,看行为是否对行为对象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且不法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长时间的非法拘禁行为很容易导致被害人身心不全、精神恍惚等自身素质严重下降的结果,而此时继续的非法拘禁行为本身和被害人自身素质相结合,就会产生被害人自伤自残或是急于摆脱非法迫害而轻生的风险,行为人应当有义务阻止该风险的实现,如果该风险发生,则认为行为人的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自杀死亡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要承担结果加重犯的责任。[17]可见,仅就被害人自杀身亡而言,该种观点认为,只有被害人自身身心不健全的,对被告人才可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否则,如果被害人身心健全,则应自我负责,被告人不负责任。这种观点区分归因与归责两个层次,是符合因果关系理论发展实际的,应当说思考方向是对的。不过,仍然值得商榷。
第一,如何判定被害人是否身心健全、判定标准及判定主体是谁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估计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对此亦无然为力,采用此标准难免陷入恣意判断。因此,同前两种观点一样,该观点面临着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第二,客观归责理论所提归责原则之一,是结果与危险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常态的关联性,否则,如果结果与危险行为之间产生重大偏离,或者说结果与危险行为之间只是一种不寻常的结合,则应当排除归责。[18]所谓“常态关联性”,不过是一种相当性,即在通常情况下,是否有此行为即会有此结果。[19]而一定能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身心不健全的被害人自杀之间具有相当性吗?恐怕未必,自杀者毕竟占极少数。
第三,非法拘禁行为能否使被害人自杀的风险提高,行为人能否掌控其中的因果历程因而可以归责,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毕竟,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自杀者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害人不会选择自杀。
第四,能否适用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来排除身心不健全者场合的客观归责,也值得考虑,毕竟被害人是“出于有意识且负责地实现自我损害或者自我危险”的。换言之,被害人是自杀的,不是被行为人杀死的,应当自己对其死亡结果负责。例如在【案例3】中,虽然学生身心发育还不够健全,但是,该教师仅是将其锁在教室内令其补做作业,并未实施其他行为,让他对学生的自杀身亡承担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未必合适。
第五,同前面几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遗漏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即使肯定被告人要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责,也不意味着必须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负责,而有可能应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负责。
第六,上述论者认为,因为身心不健全者很可能自杀,故被告人有义务保障被害人不致自杀。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既然对身心健全者的自杀都不用负责,何况对身心不健全者的自杀?要知道,引起身心健全者自杀要比引起身心不健全者自杀困难得多,说明其非法拘禁行为对被害人意志的推殘程度更严重,更应当严惩。
综上所述,除了全面肯定说认为非法拘禁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外,其余各种观点都企图在肯定条件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被告人进行结果加重犯归责的标准,如直接性要件、主要原因、直接的、必然的原因、被害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被害人因身心发育不健全而自杀等,但是,无论哪种观点都存在不妥之处,均无法圆满解决对被害人自杀的非法拘禁案件的定性问题。
三、非法拘禁的行为人负有防止被害人自杀的作为义务
可见,目前各种学说,无论从因果关系立论,还是从客观归责立论,都无法圆满解决非法拘禁致人自杀案件的定性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自杀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对行为人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论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未区分结果加重犯与实质的数罪,存在将因果关系、结果加重犯和实质的数罪混为一谈的问题,二是容易导致刑罚过于严苛,如同【案例3】那样。实际上,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非法拘禁行为,另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或过失致人死亡行为,本不符合“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之结果加重犯特征,而是实质的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因为,鉴于被害人自杀时的特殊环境,即被害人自杀时处于一种除非法拘禁行为人之外他人无法救助、无法制止的封闭环境中这一事实,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负有保护义务,有义务防止被害人自杀或他杀事件的发生。
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其中,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或者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是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危害行为。例如,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有生命危险时,肇事者有义务立即将被害人送医院救治。先行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既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20]显然,应当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人负有防止被害人自杀的作为义务,因为被害人的自杀意图是非法拘禁行为引起的,正是非法拘禁才使被害人陷入自杀危险之中,两者之间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因果关系,这种事实因果关系是难以否认的。
而非法拘禁仅仅是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人在此罪中的罪责仅止于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对于超出人身自由程度的其他侵犯行为,行为人仍应承担相应罪责。正如赵秉志教授所言,如果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有引发比所构成的犯罪构成所不能涵括的更为严重的其他犯罪结果的危险时,法律必须赋予其作为的义务,否则将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轻纵犯罪,例如对于使用暴力妨害公务或抗税致使公务人员受伤而不予救助,放任其死亡的,行为人负有救助义务,应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21]
因此,行为人对因非法拘禁引起的被害人自杀结果应负有防止义务,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死亡结果发生,否则,就应承担非法剥夺人他人生命权的罪责。
就先行行为的实质而言,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承认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需要先行行为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否则难以肯定不履行这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足以同相应的作为犯罪等价,但是,在被害人被非法拘禁的状态下,由于只有行为人才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被害人自杀或他杀,并且被害人自杀时非法拘禁状态仍在持续之中,所以行为人对被害人应当处于保证人地位,有义务防止被害人自杀结果发生。正如某学者所言,非法拘禁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非法拘禁期间,行为人非法限制、剥夺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致使行为人实际上负有保护被害人人身安全的特定义务,该特定义务是由行为人先前的非法拘禁行为引起的。[22]
在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自杀或者“被自杀”的案例时有发生,如果不赋予行为人对被害人自杀的防止义务,将极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生命权。特别是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因不堪忍受非法拘禁、殴打或侮辱而明确表示要自杀或正在自杀的情况下,如果认为行为人没有救助义务,可以见死不救,对其仅依非法拘禁基本犯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这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讲,都是极不妥当的。只有赋予行为人以救助义务,才能依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才能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因此,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实际上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一直持续着的非法拘禁行为,对该行为,行为人要构成非法拘禁罪;另一个是对被害人的生命安全不履行救助义务的不作为,对于该不作为,应视主观故意或过失成立相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故意不履行救助义务的,成立故意杀人罪,例如见被害人正要跳窗、正要服毒、正在上吊而不制止不救助;对被害人的自杀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例如【案例3】中教师锁门离开致使被锁学生上吊自杀,不过,由于学生上吊自杀的概率极低,不认定过失可能更加符合社会通常观念。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两个罪名之间是实质竞合关系,如果刑法中没有特别规定的话,理应数罪并罚。
四、对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的行为应数罪并罚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对于行为人所触犯的这两个罪名,是数罪并罚妥当,还是必须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定罪量刑?这得考虑“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规定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或者法律拟制的问题。
首先,仅就该规定本身而言,不宜否定它是一种结果加重犯规定。因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刑法将原本“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鉴于基本行为有导致加重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而结合规定为其中一个重罪并加重法定刑。[23]例如,故意伤害(致死)罪是一个故意伤害行为同时触犯故意伤害和过失致人死亡两个罪名,由于故意伤害行为具有引起死亡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而在立法上规定比这两个罪的法定刑总和还要重得多的刑罚;强奸(致人死亡)罪也是如此。显然,不宜否认诸如非法拘禁导致被害人冻死、饿死或病死等情况属于结果加重犯。但是,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的性质有所不同,因为行为人非法拘禁和未履行救助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是两个行为,是实质数罪而非想象竞合,不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本质,不宜认为构成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
其次,肯定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不属于结果加重犯之后,还得考虑“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规定是否法律拟制。因为,如果该规定属于法律拟制的话,则无论行为人实施了几个行为触犯了几个罪名,都要按此一拟制规定来定罪量刑。但是,由于法律拟制只是一种立法现象,对于具体条文是否属于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目前尚无比较一致的看法,加之法律拟制往往在缺乏相应罪过的情况下改变定性,比如将过失致人死亡罪拟制为故意杀人罪,将故意毁坏财物罪拟制为抢劫罪等,天然地存在着违背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问题,所以应尽量限制法律拟制的认定范围。况且,如果认为它属于法律拟制,则其一概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认定结果,与前述全面肯定说的结论是一样的,因此也存在着违背公平正义的缺陷。因此,笔者倾向于排除法律拟制的看法,实际上目前尚未有人认为它属于法律拟制。
再次,就此类案件而言,数罪并罚比单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更能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为,非法拘禁基本犯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不作为故意杀人一般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法定刑为3年至10年,[24]数罪并罚,可决定执行3至13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3年以上7年以下,与非法拘禁数罪并罚,可决定执行3至10年有期徒刑;无论哪种并罚,都无疑比一律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案件的各种情况、更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量刑结果上也能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之结果加重犯和“使用暴力致人死亡”之转化犯达到均衡。
最后,在有足够理由推断被害人并非自愿自杀,而是被非法拘禁者胁迫而自杀或故意杀害,但证据又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亦可认定行为人成立通常情节的故意杀人罪,对其判处10年以上刑罚,再与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这样既有利于严惩非法拘禁过程中的故意杀人犯,又有利于预防更多被害人生命权遭受非法剥夺,完全符合风险社会中强化社会保护机能的刑法发展趋势。
综上,在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的案例中,行为人不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而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基本犯和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数罪并罚。
【注释】
[1] 刑法第238条规定:“(1)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2)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案情:2008年9月,被害人景某为玩赌博机向被告人王某借高利贷6000元,利息900元先从本金中扣除,约定当日偿还。当晚23时许,景某被王某等人押送至其朋友家借钱未果,趁押送人不注意,从三楼楼道口跳窗身亡。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刑初字第588号刑事判决书。上海法院网http://www.hshfy.sh.cn:8081/flws/text.jsp?pa=ad3N4aD0xJnRhaD2jqDIwMDmjqcbW0Myz9dfWtdo1ODi6xSZ3ej0Pdcssz,2016-3-18。
[3] 案情:2009年2月,被害人吴某向被告人郭某借高利贷10万元,先行扣除3万元利息,实际到手7万元,约定借期一个月。借期届满之后,吴某因无力还贷而四处躲藏。同年4月,郭某等人找到吴某,将其带至某宾馆客房内看管并向吴某索要欠款。期间,吴某打电话让家里人帮其还钱,因其妻与其兄表示无力还款而未果。随后,吴某于当晚20时许跳窗坠楼身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刑终字第3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上海法院网 http://www.hshfy.sh.cn:8081/flws/text.jsp?pa=ad3N4aD03Njg0MzkmdGFoPaOoMjAxMKOpu6a2/tbQ0MzW1dfWtdozNzi6xSZ3ej0Pdcssz,2016-3-18。
[4]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马克昌:《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869页。
[5] 此案例案号为: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2000)唐刑初字第070号刑事判决书,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网http://www.linklaw.com.cn/chinacase/al_content.asp?id=2306,2016-3-18。
[6] 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91页、第169-170页。
[7] 李邦友:《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8] 同前引[6],第184页、第176页。
[9] 孙运梁:《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类型化研究》,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1期。
[10] 李磊:《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司法认定——兼论刑法第238条第2款》,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4期。
[11] 王敬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司法认定》,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12]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13] 同前引[6],第176页。
[14] 该文引用了一则案例:甲欠乙、丙10万元工程保证金,乙、丙多次讨要未果,于是将甲叫到宾馆索要10万元债务,将甲围困在宾馆房间寸步不离。甲终因精神压力过大趁二人不备时跳楼身亡。作者认为,乙和丙并不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因为甲是身心健全的人,对于身心健全的人故意自伤、自杀或被其他人故意伤害或杀害的,可以考虑因果关系的断绝,而仅成立普通的非法拘禁罪。这是对客观归责理论存在误解,因为客观归责理论并不承认所谓因果关系断绝,而是肯定因果关系但否认客观归责。因果关系断绝(或中断)是早期部分条件说者所持的观点。
[15] 该作者所举案例:行为人于甲患病时,因甲乱丢烟蒂忿加捆缚后,下楼赌博多时,始行释放,以致甲深受寒冷,病势陡剧,不及医治身死。因为非法拘禁行为排除了患病的被害人躲避受冷的条件,导致被害人病情加重死亡。
[16] 陈山:《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的规范诠释》,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7] 王麒锟、徐国朋:《非法拘禁期间被害人自杀死亡的认定》,载《江苏法制报》2013年12月12日,第4版。
[18] 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55页;林山田:《刑法通论(上)》,林山田自版发行2008年版,第228页。
[19] 林山田、许泽天:《刑总要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92、94、97页。
[20]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
[21] 赵秉志、肖中华、左坚卫:《刑法问题对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22] 张永东:《非法拘禁期间被害人逃跑坠楼身亡如何定罪》,载《法制生活报》2014年2月28日,第3版。
[23] 周铭川:《结果加重犯争议问题探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24]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践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故意杀人罪,大多以“情节较轻”为由判处3至8年有期徒刑,笔者至今尚未见到一例判刑超过8年的,毕竟“见死不救”的危害性比积极作为杀人的小很多,客观上行为人只是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已。
【作者简介】黄丽勤, 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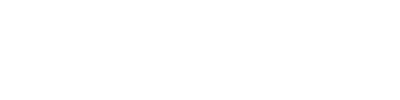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