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
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然而从1983年开始我国实行“严打”刑事政策,因而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遭遇强大的阻力。虽然立法上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则往往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而将防卫过当认定为普通犯罪,因而正当防卫制度未能发挥其法律效果。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对正当防卫作了较大的修改,尤其是引人注目地增设了无过当防卫制度。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在上述规定中,第一款是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第二款是关于防卫过当的规定,第三款是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从逻辑关系上来说,第三款是第二款的例外规定。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在一般情况下存在防卫过当,但在符合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则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
无过当之防卫是针对特定犯罪适用的,这些犯罪是指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立法机关之所以作出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考虑了当前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当前,各种暴力犯罪猖獗,不仅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也严重威胁公民的人身安全,对上述严重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作出特殊规定,对鼓励群众勇于同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考虑了上述暴力犯罪的特点。这些犯罪都是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被侵害人面临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很难辨认侵害人的目的和侵害的程度,也很难掌握实行防卫行为的强度,如果对此规定得太严,就会束缚被侵害人的手脚,妨碍其与犯罪作斗争的勇气,不利于公民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修改刑法时,对一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了不存在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定。{1}立法机关的这一考虑当然有其合理性,尤其是考虑到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案件的认定出现严重偏差。
当然,这一规定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对此,我国学者进行了批评,认为特别防卫权的立法化,不仅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着弊端,而且因防卫权异化的不能完全避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潜藏着破坏法治秩序的危险。{2}这一批评不无道理。然而,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引起我思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立法与司法的分野,以及立法的限度问题。诸如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这样一些问题,在立法上只能作出概然性规定,具体的裁量权由司法机关行使。
在这个意义上说,1997年刑法修订前,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正当防卫案件在认定上出现的偏差并非立法的责任,而是司法的问题,尤其与“严打”的刑事政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立法机关试图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我国学者亦有肯定的观点,认为无过当防卫之规定把原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问题,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做显然对于公民大胆行使防卫权和司法机关处理案件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利于贯彻正当防卫的立法主旨。{3}这里其实涉及立法的限度问题。我认为,立法总是针对一般情形的,因而具有抽象性;而司法是针对个别案件的,因而具有具体性。立法不应、也不能替代司法的判断。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虽然在强化公民防卫权方面有所得,但在防止防卫权滥用方面必有所失。这里的得失平衡,不可能由立法来获得,而是应当通过司法活动来达致。
一、叶永朝故意杀人案{4}:无过当防卫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界定
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尽管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无过当之防卫作了明确规定,但该款规定在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问题。叶永朝故意杀人案就是在刑法修订后适用无过当之防卫规定的第一案,从这个案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无过当之防卫认定上所做的努力。
被告人叶永朝,男,1976年7月30日生。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7年2月21日被逮捕,同年5月21日被监视居住。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以叶永朝犯故意杀人罪,向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1月上旬,王为友等人在被告人叶永朝开设的饭店吃饭后未付钱。数天后,王为友等人路过叶的饭店时,叶向其催讨,王为友认为有损其声誉,于同月20日晚纠集郑国伟等人到该店滋事,叶持刀反抗,王等人即逃离。次日晚6时许,王为友、郑国伟纠集了王文明、卢卫国、柯天鹏等人又到叶的饭店滋事,以言语威胁,要叶请客了事,叶不从,王为友即从郑国伟处取过东洋刀往叶的左臂及头部各政一刀。叶拔出自备的尖刀还击,在店门口刺中王为友胸部一刀后,冲出门外侧身将王抱住,两人互相扭打政刺。在旁的郑国伟见状即拿起旁边的一张方凳砸向叶的头部,叶转身还击一刀,刺中郑的胸部后又继续与王为友扭打,将王压在地上并夺下王手中的东洋刀。王为友和郑国伟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也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王为友全身八处刀伤,左肺裂引起血气胸、失血性休克死亡;郑国伟系锐器刺戳前胸致右肺贯穿伤、右心耳创裂,引起心包填塞、血气胸而死亡;叶永朝全身多处伤,其损伤程度属轻伤。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永朝在分别遭到王为友持刀政、郑国伟用凳砸等不法暴力侵害时,持尖刀还击,刺死王、郑两人,其行为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7年10月14日判决如下:被告人叶永朝无罪。
一审宣判后,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其主要理由是:叶永朝主观上存在斗殴的故意,客观上有斗殴的准备,其实施行为时持放任的态度,其行为造成二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叶永朝的犯罪行为在起因、时机、主观、限度等条件上,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永朝在遭他人刀政、凳砸等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时,奋力自卫还击,虽造成两人死亡,但其行为仍属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8年9月29日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在叶永朝案中,死者系滋事方,并且是持刀在叶永朝的饭店行凶,在这种情况下被叶永朝杀死。因此我认为,即使没有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也应认定为正当防卫。我关注的不是这样的案件法院为什么判决无罪,而是关注这样一件正当防卫的案件检察机关为什么作为防卫过当起诉到法院。对于本案,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认为,叶永朝对不法侵害进行防卫,使用凶器致二人死亡,其行为虽属正当防卫,但已超过必要限度,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在抗诉时,检察机关又认为,叶永朝有斗殴的故意,有斗殴的准备,持放任态度,造成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5}应该说,检察机关对无过当之防卫的理解是存在错误的,主要在于行为性质上的混淆。叶永朝是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所进行的防卫行为,但检察机关却认为是斗殴。如何区分正当防卫与互相斗殴,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正当防卫与斗殴确实十分相似,两者区分的关键在于起因。如果是由于一方的不法侵害引起他方的防卫,防卫方的行为就不能认为是斗殴,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当然,由于本案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而一审判决则是在1997年刑法生效后,公诉机关对刑法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不熟悉,这是一个可能的理由。无论如何,即使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如果司法机关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其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当然,在叶永朝案中,法院还是正确地适用了刑法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规定。
叶永朝案涉及的问题在于:如何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虽然对无过当之防卫的暴力犯罪作了列举,但这些暴力犯罪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对之实行无过当之防卫。对此,裁判理由指出:
叶永朝在防卫行为开始前和开始防卫后,身受犯罪分子行凶伤害致轻伤,能否认定王为友等人的行为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首先,法律并未规定特殊防卫的行为人必须身受重伤、已被抢劫、强奸既遂等才可以进行防卫,因此,叶永朝身受轻伤,足以表明对方侵害的严重暴力性质。其次,防卫的目的恰恰是使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不能得逞,因此,即使防卫人根本没有受到实际伤害,也不应当影响特殊防卫的成立;再次,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侵犯防卫人的行为客观存在。本案中王为友等人手持东洋刀,且已砍在防卫人身上,如不对其进行更为严重的反击,如何制止其犯罪行为?因此,行为人放任甚至希望将对方刺伤、刺死,在适用本条款规定时,不应成为障碍。因为叶永朝在受到严重人身侵害的情况下防卫,是法律允许的,具有正义性,虽造成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仍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故不负刑事责任。一、二审法院的判决、裁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该款规定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是人民群众同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但在实际审判业务中,此类案件往往情况复杂、造成的后果严重,因此要注意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把握住正当防卫的正义性这一基本要素,排除防卫挑拨、假想防卫等情况,既要保护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为,又要防止坏人假借防卫而犯罪,以体现刑法本条款的立法原意。
以上裁判理由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无过当之防卫的前提条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裁判理由的有关精神,我认为在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这一要件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人身侵害性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只有对侵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才能实行无过当之防卫。由此可见,刑法中的无过当之防卫,主要是为使人身安全不受暴力侵害而设置的一种特殊防卫制度。因此,在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时候,应当注意暴力犯罪具有对人身的侵害性。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了列举,包括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在这些犯罪中,杀人、强奸、绑架都属于刑法所规定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因而具有人身侵害性,这是没有问题的。抢劫在刑法中属于侵犯财产罪,但刑法学界通常认为,抢劫罪具有侵犯财产权利与侵犯人身权利的双重属性,因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具有暴力性,它严重侵害了财产所有人和保管人的人身权利,以此达到将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的目的。如果是单纯地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例如盗窃、抢夺和诈骗等犯罪,因这些犯罪不具有人身侵害性,因而对之不能实行无过当之防卫。当然,在实施上述犯罪的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转化为抢劫罪,对之可以实行无过当防卫。值得注意的是,叶永朝案的裁判理由指出:“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指这四种犯罪行为,也包括以此种暴力性行为为手段,而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行为,如以抢劫为手段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行为,以绑架为手段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此外,针对人的生命、健康采取放火、爆炸、决水等其他暴力方法实施侵害,也是具有暴力性的侵害行为。”我认为,以上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它为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确定了范围,具有参考价值。
(二)现实危害性
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某些情况下是指已经造成他人的人身侵害后果,例如致人伤亡等。但并非只有已经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法侵害人没有造成人身侵害后果,但具有造成人身侵害后果的危险性,也同样可以认定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采用的是“危及”一词,该词本身具有已经存在现实危险的含义。在叶永朝案中,不法侵害人王为友等已经造成了叶永朝轻伤,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具备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要件。
(三)程度严重性
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明确地标示了这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必须达到严重程度。如果虽然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但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仍然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而不能实行无过当之防卫。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程度,以便确定是否可以对之实行无过当之防卫?我认为,这主要应当从双方人数多寡、对方是否携带凶器、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各种情况加以综合考察。在叶永朝案中,王为友吃饭后不但不还欠款,在被合理追索欠款后,还纠集多人,携带凶器到叶永朝开设的饭店寻衅滋事,并持刀将叶砍伤。这一暴力犯罪已经对叶永朝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侵害,因而叶永朝实行的防卫属于无过当之防卫,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二人死亡的后果,也不负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二、李小龙等故意伤害案{6}:无过当防卫之“行凶”的理解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无过当之防卫的防卫客体规定中,杀人、抢劫、强奸、绑架都是刑法中正式的罪名,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把握。但与上述四种罪名相并列的“行凶”,并不是刑法中正式的罪名,因而如何正确理解,就存在问题。对于如何理解这里的“行凶”,在叶永朝案的裁判理由中就曾经论及,认为“行凶”行为仅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法伤害行为,如使用凶器暴力行凶,有可能致人重伤的伤害行为。这一裁判理由,将“行凶”明确地界定为伤害。但为什么在法条中不直接表述为“伤害”,而是采用“行凶”这一措词呢?对此,我国学者大多持一种批评态度。例如学者指出:
现行刑法在特别防卫权的规定中使用“行凶”一词不妥。这是因为,首先,严格说来,行凶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将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其他罪名并列在一起,不符合逻辑要求。其次,根据前所述及的“行凶”一词的本意,“行凶”一般是指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行为。而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表明这里的“行凶”是不包括杀人行为在内的。那么,伤害行为、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行为是否包括在“行凶”之内呢?对此,法律没有明确的说明,这难免导致人们在理解上发生歧义。再次,从立法上规定特别防卫权的宗旨出发,“行凶”必须是程度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否则,不能进行特别防卫。既然如此,“行凶”完全可以为后面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包容。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关于“行凶”的规定,未免多余,有重复规定之嫌。{7}
以上对立法关于“行凶”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当然,刑法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还只能通过解释刑法明确其含义,从而为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无过当之防卫提供法理根据。正因为刑法采用了“行凶”这样一种较为含混的用语,因而我国刑法学界对“行凶”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歧义。例如,我国学者在界定“行凶”时,强调行凶者主观上犯意的不确定性,即行凶者具有实施刑法上的杀人罪或者伤害罪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致防卫人难以识别,就是行凶者自己忙乱之中也未及确定。即行凶者自己在实施行凶行为时,也存在着或死或伤他人的随机性,刑法学理上又谓之“放任故意”。这种放任,正是“行凶”与单纯的杀人或单纯的伤害之区别所在。根据这种见解,刑法意义的行凶是指对他人施以致命暴力的、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8}这种观点将行凶定义为伤害与杀人之间界限不明确的一种暴力性犯罪,既非典型的伤害也非典型的杀人。张明楷教授亦持这一观点,认为行凶包含了杀人与界限不明,但有很大可能是造成他人眼中的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9}当然,我国也有学者不是这样认识的,而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行凶。例如,刘艳红教授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刘艳红教授揭示了“行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行为内容的暴力性;(2)暴力的手段不限定性;(3)暴力程度的严重性;(4)暴力行为的无法具体罪名性。{10}在以上四个特征中,刘艳红教授更为强调的是无法具体罪名性,即未显示出完全符合某一个暴力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行凶具有犯意上的不明确性与犯行上的不明确性。应当指出,在不明确性这一点上,认识是共同的。但这种不明确的范围究竟如何确定,则存在一些差别。张明楷教授将行凶的不明确性限于伤害与杀人之间,而刘艳红教授则作了较为广义的理解,在举例时指出:夜间以实施某种犯罪为目的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在不法侵害人开始实施进一步的犯罪行为之前,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具体罪名。但是,对于依然安睡的住宅主人而言,该行为往往会造成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使得他们可能会实施正当防卫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11}但在上述深夜侵入他人住宅而又尚未进一步实施具有侵害行为的情况下,能否认定为刑法中的“行凶”,这是值得质疑的。若对“行凶”作如此广义的理解,有悖于立法意图。正因为我国刑法学界对“行凶”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因而李小龙案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行凶”具有指导意义。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武威分院以被告人李小龙、李从民、李小伟、靳国强、李凤领犯故意伤害罪向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8月13日晚21时许,河南省淮阳县春蕾杂技团在甘肃省武威市下双乡文化广场进行商业演出。该乡村民徐永红、王永军、王永富等人不仅自己不买票欲强行入场,还强拉他人入场看表演,被在门口检票的被告人李从民阻拦。徐永红不满,挥拳击打李从民头部,致李倒地,王永富亦持石块击打李从民。被告人李小伟闻讯赶来,扯开徐永红、王永富,双方发生厮打。
其后,徐永红、王永军分别从其他地方找来木棒、钢筋,与手拿鼓架子的被告人靳国强、李凤领对打。当王永富手持菜刀再次冲进现场时,赶来的被告人李小龙见状,即持“T”型钢管座腿,朝王永富头部猛击一下,致其倒地。王永富因伤势过重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王永富系外伤性颅脑损伤,硬脑膜外出血死亡。徐永红在厮打中被致轻伤。
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小龙、李从民、李小伟、靳国强、李凤领在遭被害人方滋扰引起厮打后,其行为不克制,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后果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李小龙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持械殴打致人死亡,系本案主犯,应从严惩处。被告人李从民、李小伟、靳国强、李凤领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本案从犯。考虑被害人方在本案中应负相当的过错责任,对各被告人可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二款、第二十五条一款、第二十六条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于2001年6月22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李小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2.被告人李从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3.被告人李小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4.被告人靳国强、李凤领犯故意伤害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上述各被告人均以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一方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合法演出单位。被害人一方既不买票,又强拉他人入场看表演。被告人李从民见状要求被害人等人在原来票价一半的基础上购票观看演出,又遭拒绝,并首先遭到徐永红的击打,引发事端。双方在互殴中,被害人持木棒、钢筋等物殴打上诉人。当王永富持菜刀冲进现场行凶时,被李小龙用钢管座腿击打到头部,致其倒地。此后,李小龙等人对王永富再未施加伤害行为。王永富的死亡,系李小龙的正当防卫行为所致。徐永红的轻伤系双方互殴中所致。本案中,被害人一方首先挑起事端,在实施不法侵害行为时,使用了木棒、钢筋、菜刀等物,其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无论强度还是情节都甚为严重;并且在整个发案过程中,被害人一方始终未停止过不法侵害行为,五上诉人也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了无过当防卫条款,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其目的就是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五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其主张正当防卫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三款之规定,于2002年11月14日判决如下:
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小龙、李从民、李小伟、靳国强、李凤领宣告无罪。
在李小龙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作出了有罪与无罪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决。一审法院虽然认定对方滋扰引起厮打、过错在先,但又认为被告人李小龙等人行为不克制,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因而构成故意伤害罪。关键是:对方的滋扰是否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行凶”,如果属于“行凶”,则李小龙等人的行为是对“行凶”的无过当防卫,不能认定为犯罪。显然,一审法院并不认为对方的滋扰属于“行凶”,因而认定李小龙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二审法院则认定对方持木棒、钢筋等物殴打李小龙等人,其中王永富持菜刀冲进现场行凶,因而认定李小龙等人的行为构成无过当之防卫。李小龙案的裁判理由对如何理解刑法中的“行凶”有借鉴意义,结合本案作了以下阐述:
对以暴力实施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行为可以实施特殊防卫,比较容易把握。但是何谓“行凶”呢?我们认为,对“行凶”的理解应当遵循上述关于特殊防卫条件的基本认识,即首先,“行凶”必须是一种已着手的暴力侵害行为;其次,“行凶”必须足以严重危及他人的重大人身安全。故“行凶”不应该是一般的拳脚相加之类的暴力侵害,持械殴打也不一定都是可以实施特殊防卫的“行凶”。只有持那种足以严重危及他人的重大人身安全的凶器、器械伤人的行为,才可以认定为“行凶”。
本案中,被害人一方仗势欺人,滋事生非,自己既不买票,还强拉他人入场看表演。当被告人李从民为息事宁人作出让步,要求被害人等人在原来票价一半的基础上购票看演出时,又首先遭到被害人方的不法侵害。在被告人方进行防卫反击时,被害人一方又找来木棒、钢筋、菜刀等足以严重危及他人重大人身安全的凶器意欲进一步加害被告人方,使被告人方的重大人身安全处于现实的、急迫的、严重的危险之下,应当认定为“行凶”。此时,被告人李小龙为保护自己及他人的重大人身安全,用钢管座腿击打王永富的头部,符合特殊防卫的条件,虽致王死亡,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本案其他被告人在防卫反击中,致徐永红轻伤,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也未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大损害,故同样不负刑事责任。二审法院依法宣告本案各被告人无罪的判决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裁判理由,在认定刑法中的“行凶”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暴力侵害性
“行凶”属于暴力犯罪行为,具有暴力侵害性,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行凶”虽然未归入某一个具体的侵犯人身权利罪的罪名,但其具有对他人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性,属于暴力犯罪的范畴,对此,在无过当之防卫中应当严格加以把握。因此,如果仅仅是一般的口头威胁、谩骂等,都不能认定为“行凶”。
(二)着手实行性
“行凶”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已经着手实施的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侵害行为,应当强调其具有着手实行的性质,而不是着手实行以前的行为。例如上述刘艳红教授所说深夜潜入他人住宅,这是一种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如果事主发现,当然可以对之实行正当防卫,但这不属于无过当之防卫。如果潜入他人住宅以后又对事主实行了暴力侵害,那就可以根据其暴力侵害的程度认定为“行凶”,事主对之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对一般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之所以不能认定为“行凶”,就在于行为人尚未着手实施暴力侵害行为。因此,“行凶”的不明确性,主要是指对造成死亡还是伤害结果的不明确,而不是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暴力侵害性的不明确。
(三)程度严重性
“行凶”所具有的对人身安全的危险,具有未然性,是一种现实危险性。因此,“行凶”是否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确实不太容易掌握。例如,在邓玉娇防卫过当案中,邓玉娇因受邓贵大等人的滋扰,持刀将邓贵大刺死,并将上前阻拦的黄德智刺伤。辩护人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而法院判决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行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了防卫限度,属于防卫过当,邓玉娇的行为构成犯罪。关于本案,邓贵大、黄德智确实有对邓玉娇的滋扰行为,主要表现在要求正在宾馆洗衣的服务员邓玉娇为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被拒后,对邓进行拉扯、辱骂,邓玉娇两次欲离开房间,均被邓贵大拉住并推倒在身后的单人沙发上。倒在沙发上后,邓玉娇朝邓贵大乱蹬,将邓贵大蹬开,当邓贵大再次逼近邓玉娇时,邓玉娇起身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邓贵大刺伤致死,并将黄德智刺伤。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认定邓贵大等人欲对邓玉娇进行强奸,而且其拉扯、推到、辱骂行为,尚不属于“行凶”,因此不能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无过当之防卫。虽然法院认定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该防卫行为已经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构成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防卫过当。这一认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应当把一般性地打架,即拳打脚踢与“行凶”加以区分。我认为,“行凶”是指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即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12}因此,我强调“行凶”必然以使用凶器为前提,这里的凶器,应作广义理解,包括使用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凶器,也包括使用其他可以用于人身侵害的其他器械,例如棍棒、砖石等。如果没有动用凶器,指使拳脚相加的殴打,不能认定为“行凶”。当然,也不能认定为只要使用凶器就一定构成“行凶”,还要考虑是否达到对人身安全造成侵害的严重程度。因此,使用凶器是认定“行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在李小龙案中,对方使用木棒、钢筋、菜刀等足以严重危及他人重大人身安全的凶器意欲进一步加害被告人方,因此属于“行凶”,对李小龙等人的反击行为认定为无过当之防卫,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三、吴金艳故意伤害案{13}:无过当防卫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认定
无过当之防卫在司法认定中首先涉及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防卫客体的举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有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这是从无罪推定原则引申出来的结论。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不仅应当收集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也应当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因此,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控方应当对是否存在防卫情节进行查证。如果查证属实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就应当作出相应的处理。当然,如果未能查证属实的,则仍然依法提起公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按照无过当防卫进行辩护的,无过当防卫致人伤死就成为一个无罪辩护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是否存在无过当防卫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防卫客体,就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举证。对此,我国学者指出:“对于特别防卫案件,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当然要全面收集证据。但被告人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特别防卫主张,同样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否则,被告人尽管提出自己的行为属于特别防卫,但被告人既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也没有发现有关特别防卫的事实材料的,就不能认定特别防卫的成立,防卫人就应当对自己所实施的造成他人伤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4}我认为,以上观点是正确的。当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无过当防卫的辩护理由如何进行甄别采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吴金艳案中,围绕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证据采信展开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金艳犯故意伤害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2003年9月10日凌晨3时许,被害人李光辉(男,19岁)与孙金刚(男,22岁)、张金强(男,21岁)到北京市海淀区阳台山庄饭店的女工宿舍外,叫服务员尹小红(女,24岁)出来解决个人之间的纠纷,见尹小红不予理睬,孙金刚等人即强行进入宿舍内。孙金刚与尹小红发生争执,殴打尹小红。同宿舍居住的被告人吴金艳上前劝阻,孙金刚又与吴金艳相互撕扯。在撕扯过程中,孙金刚将吴金艳的上衣纽扣拽掉,吴金艳持水果刀将孙金刚的左上臂划伤。李光辉见此状况,用一铁挂锁击打吴金艳,吴金艳又持水果刀扎伤李光辉的左胸部,致其左胸部2.7厘米刺创口,因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当日,吴金艳被公安机关抓获,作案工具亦起获。吴金艳无视国法,因琐事故意伤害公民身体健康,且致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判处。
被告人吴金艳辩称:孙金刚殴打、欺辱并要强奸尹小红,我过去劝阻,孙金刚即又殴打、欺辱我,将我的上衣撕开,上身裸露,使我感到很屈辱。我认为孙金刚要强奸我,为了防卫才拿起刀子。这时,李光辉用铁挂锁来砸我,我才冲李光辉扎了一刀。如果孙金刚和李光辉不对我和尹小红行凶,我不会用刀扎他们。李光辉是咎由自取,应自己承担损失。吴金艳的辩护人认为,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吴金艳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不构成犯罪,也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公诉人答辩如下:被害人李光辉虽然是与孙金刚一同进入女工宿舍,但没有对尹小红、吴金艳实施任何伤害行为。李光辉拿锁欲击打吴金艳,是为了制止孙金刚与吴金艳之间的争斗。吴金艳虽然受到孙金刚的攻击,但当时她有多种求助的选择。况且李光辉等人的行为没有达到严重危及吴金艳等人人身安全的程度,没有危害后果产生。故吴金艳持刀扎伤李光辉,不属于正当防卫。考虑到被害人一方的行为也属于不法行为,存在较大过错,吴金艳的认罪态度较好,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以上控辩双方对案情的叙述并不完全相同。控方强调孙金刚殴打了尹小红,在吴金艳劝阻时又与吴发生撕扯。在这种情况下,吴金艳持刀将孙金刚划伤。李光辉见此状况用铁挂锁欲击打吴金艳时,吴又持刀扎上李光辉,后不治身亡。而被告人吴金艳则指述,孙金刚要强奸尹小红,在劝阻中被孙殴打,为防卫才拿刀扎孙。当李光辉用铁锁砸来时又扎李光辉一刀。在以上叙述中,孙金刚殴打尹小红可以确定。至于吴金艳前来劝阻时,两人是撕扯,还是孙金刚殴打吴,则各执一词。李光辉用铁锁砸吴金艳,这也是事实,但控方认为李光辉等人的行为没有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其根据是没有后果产生,这一观点颇有唯结果论的意味。其实,行凶并以不发生实害结果为认定的必要条件。关于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以下认定:
孙金刚等人在凌晨3时左右闯入女工宿舍后,动手殴打女服务员,撕扯女服务员的衣衫,这种行为足以使宿舍内的三名女服务员因感到孤立无援而产生极大的心理恐慌。在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被告人吴金艳持顺手摸到的一把水果刀指向孙金刚,将孙金刚的左上臂划伤并逼退孙金刚。此时,防卫者是受到侵害的吴金艳,防卫对象是闯入宿舍并实施侵害的孙金刚,防卫时间是侵害行为正在实施时,该防卫行为显系正当防卫。
当孙金刚被被告人吴金艳持刀逼退后,李光辉又举起长11厘米、宽6.5厘米、重550克的铁锁欲砸吴金艳。对李光辉的行为,不应解释为是为了制止孙金刚与吴金艳之间的争斗。在进入女工宿舍后,李光辉虽然未对尹小红、吴金艳实施揪扯、殴打,但李光辉是遵照事前的密谋,与孙金刚一起于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女工宿舍的。李光辉既不是一名旁观者,更不是一名劝架人,而是参与不法侵害的共同侵害人。李光辉举起铁锁欲砸吴金艳,是对吴金艳的继续加害。吴金艳在面临李光辉的继续加害威胁时,持刀刺向李光辉,其目的显然仍是为避免遭受更为严重的暴力侵害。无论从防卫人、防卫目的还是从防卫对象、防卫时间看,吴金艳的防卫行为都是正当的。由于吴金艳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实施防卫,故虽然造成李光辉死亡,也在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法律许可的幅度内,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金艳于夜深人静之时和孤立无援之地遭受了殴打和欺辱,身心处于极大的屈辱和恐慌中。此时,李光辉又举起铁锁向其砸来。面对这种情况,吴金艳使用手中的刀子进行防卫,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要求吴金艳慎重选择其他方式制止或避免当时的不法侵害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具体侵害的情节等客观因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吴金艳及其辩护人关于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亦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纳。起诉书指控吴金艳持刀致死李光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据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于2004年7月29日判决:一、被告人吴金艳无罪。二、被告人吴金艳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对于本案的认定,在总体上确认孙金刚、李光辉等人在凌晨闯入女工宿舍殴打女服务员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吴金艳对孙金刚的防卫系正当防卫。但判决未能明确这一防卫是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还是第三款规定的无过当防卫。因为在此时,孙金刚并未携带凶器进行侵害,吴金艳持刀将孙扎伤,似应认定为普通正当防卫而非特殊正当防卫,因为只是将孙划伤,因而其防卫行为没有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
此后,李光辉举起铁锁欲砸吴金艳,对于这一行为如何认定,直接关系到本案定性。控方认为李光辉拿锁击打吴金艳是为制止孙金刚与吴金艳之间的争斗,但法院判决则认为这是对吴金艳的继续加害,因而属于“行凶”。考虑到夜深人静之时和孤立无援之地这样一种特殊的时间与地点受到不法侵害,法院判决认为李光辉的行凶已经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因而认定吴金艳构成无过当之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认为,法院判决对本案的无过当之防卫的认定是正确的。
结语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检察机关都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否认其行为的防卫性。但法院都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为无过当之防卫,从而宣告无罪。应该说,法院对无过当之防卫的要件把握是较为准确的。正确地区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保障公民的防卫权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刊物发表以后,对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适用无过当防卫的规定,具有指导意义。同时,这些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为正确理解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提供了实际素材。在此基础上,我国刑法学界应当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从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无过当防卫的理论。
注释:
{1}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2}参见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3}参见段立文:《对我国传统正当防卫观的反思——兼谈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修订完善》,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1辑(总第6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10页。
{5}参见王幼璋主编:《刑事判案评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5集(总第34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3页。
{7}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8}参见屈学武:《正在行凶与无过当防卫权——典型案例评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10}刘艳红:《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次实证考察》,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1}刘艳红:《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次实证考察》,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2}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
{14}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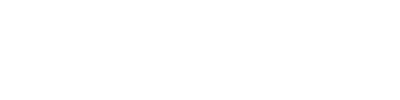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