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宁
【摘要】 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关于符合的认定标准可谓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为抽象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在解决抽象的事实错误方面,抽象符合说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规范故意”与“可罚故意”二分化的思路,而法定符合说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了罪质共通性的判断标准。“可罚故意”为认定不同犯罪类型的归属性提供了可能,罪质共通性的判断则为归属性的认定提供了标准。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可能符合的犯罪类型必须在罪质上具备实质共通性,具体包括如下两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犯罪之间,即在形式上包摄并且在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一般犯罪与兜底犯罪之间,即在形式上不包摄但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在认定这一类犯罪的抽象符合时,需要借助“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
【关键词】 抽象的事实错误;抽象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可罚故意;罪质共通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便于展开论述,笔者先举出如下四个案例:(Ⅰ)甲为了砸坏乙的名贵跑车而扔石头,不料石头打偏将乙砸死;(Ⅱ)丙为了杀害丁而开枪,不料子弹打偏将丁的名贵花瓶打碎;(Ⅲ)戊为了盗窃普通财物而盗窃了己的皮包,不料包中只有92式手枪一把;(Ⅳ)庚为了抢夺枪支而抢夺了辛的皮包,不料包中只有金钱数万元。这四个案例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行为人意图实施的犯罪与客观上实现的犯罪之间在罪质上完全不重合;行为人意图实施的犯罪与客观上实现的犯罪之间在罪质上部分重合。但无论是在罪质完全不重合还是罪质部分重合的类型中,由于行为人意图实施的犯罪与客观上实现的犯罪分别由不同的分则条文进行规制,因此便出现了应当依据哪一条文进行处断的问题。这被称为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
所谓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也即抽象的事实错误,是指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现实所发生的事实分别属于不同的构成要件;或者说,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所发生的事实跨越了不同的构成要件,因而也被称为不同犯罪构成间的错误。{1}254关于抽象的事实错误的研究是日本刑法学的一大特色,而日本刑法学热议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实施构成重罪之行为,但行为时不知为构成重罪之事实的,不得以重罪处断。换言之,当行为人以实施轻罪事实的故意却实现了重罪事实时,不应以重罪处断。不过,问题在于,上述规定仅仅是在强调无重罪之故意时不得以重罪处断,但并不是在扩张轻罪的构成要件。{2}178因此,在实际运用时,还需要明晰如下两个问题:A.无重罪之故意时,换言之,仅有轻罪之故意时,是否必须以轻罪处断。B.以重罪之故意实现了轻罪之事实时,应当以重罪还是轻罪处断。而无论在问题A还是问题B中,还有一个共通的问题C:在以轻罪处断时,能否认定为轻罪既遂。与上述四个案例相联系,关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引发了抽象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之争,以及两种学说内部的分支学说之争。
概言之,关于抽象的事实错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刑罚的不均衡,以及罪质的重合程度。{3}319日本刑法学最初争论抽象的事实错误时,主要围绕如何解决刑罚不均衡的问题展开。首先,在以轻罪故意实现了重罪事实的案件中,例如前述案例(Ⅰ)中,甲构成损坏器物的未遂(不可罚)与过失致死罪的想象竞合。根据《日本刑法》第210条的规定,可以判处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但是,如果石头如乙所愿砸坏跑车的话,则构成《日本刑法》第261条的损坏器物罪,其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科料。如果将前者的50万日元以下罚金与后者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作比较的话,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刑罚的不均衡了。{3}320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我国刑法中。例如,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故意损坏财物罪,《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仍以上述案例(Ⅰ)为例,当石头砸坏跑车时,对甲可以判处的刑罚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与之相对,当石头打偏打死乙时,如果可以证明为“情节较轻的”,则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如果打偏的石头导致乙重伤的话,根据《刑法》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打偏的石头仅仅导致乙轻伤的话,则不构成犯罪了。将这两种情况与砸坏跑车相比,同样可以看到刑罚的不均衡问题。
因此,日本刑法学发展出了抽象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两种学说都认为此时应当对故意做抽象处理,但抽象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在形式方面,法定符合说是在特定构成要件的范围内抽象地理解故意,与之相对,抽象符合说则是超越了特定的构成要件来抽象地理解故意。在实质方面,法定符合说认为行为人是有意地实现了错误结果,而抽象符合说则认为可以因为行为人对于错误结果的故意而在法定刑内处断。{4}263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互相的论战过程中又催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支学说。下文将在研讨抽象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及其分支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理论构造。
二、抽象符合说的启示:“规范故意”与“可罚故意”的分立
抽象符合说是日本刑法学的原创,最初的创立者是新派大师牧野英一先生[1]。{5}214抽象符合说之所以能在日本发展,除了《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刺激之外,还要归功于主观主义刑法学与客观主义刑法学共同的努力。主观主义刑法学强调“行为人的危险性”,认为现实发生的结果即使是由于错误引发的,也是行为人危险性的表征,其中隐含的是行为人“意图实施某种犯罪的故意”,是一种“模糊”的犯罪故意。从这种模糊的犯罪故意中可以探究行为人的危险性,因而应当对其科处刑罚。概言之,主观主义刑法学从故意中探究结果与行为人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对个案中的意思内容进行抽象化处理。与之相对,客观主义刑法学则由于不满于法定符合说无法克服的“刑罚的不均衡现象”而支持抽象符合说。{6}198详言之,以遗弃尸体的故意但实际上遗弃了活人时,按照法定符合说将构成遗弃尸体的未遂与过失遗弃。但因为两者都不构成犯罪,故而只能认为无罪了。为了克服这种违和感,客观主义刑法学从故意中探究结果与行为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对个案中的意思内容进行抽象化处理。例如,泷川幸辰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对于行为违反条理性的认识”,并进而指出: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应当重视的是“内在于行为之中的违反条理性”的程度。{7}127-128而小野清一郎则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故意责任的本质在于反道义性的认识。{8}虽然关于故意本质的理解迥然不同,但两位客观主义大师都同样认为此时可以从行为人的故意中抽取出共通的要素——“违反条理性”或“道义责任”。因此,无论主观主义刑法学还是客观主义刑法学都以结果作为媒介,以故意作为突破口来探求处罚的可能性。其思维方式都是对结果的内容与故意的内容进行“量化”处理,而不太重视行为类型中的“质的”差别。主观主义学者重视的是“行为人的危险性”,而客观主义学者关注的则是关于“行为的违反条理性”或“反道义责任”的认识。换言之,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虽然行为类型不同,故意的实质内容也不同,但因为抽象符合说只考虑故意在量上的差异,所以故意不被阻却,而罪质的差别问题也被有意地屏蔽了。因此,抽象符合说的共通之处在于:在行为人认识到的构成要件事实与现实发生的构成要件事实相一致的限度内,可以认定故意犯的既遂。其内部的分支学说如下所示。
(一)原初学说:牧野说
如上所述,牧野英一是抽象符合说的原创者,他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着眼于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展开了论述:以犯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的事实时,构成轻罪的既遂与过失重罪的想象竞合。{9}574-575反之,以犯重罪的故意实现了轻罪的事实时,构成重罪的未遂(或不能犯)与轻罪的既遂。在两种情形中都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处断。{9}575-576因此,根据牧野说,在前述案例(Ⅰ)中,甲将构成损坏器物罪的既遂与过失致死罪的想象竞合。与之相对,在前述案例(Ⅱ)中,丙将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与过失损坏器物的既遂,因为过失损坏器物不可罚,所以仅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由此可见,关于前述问题A,牧野说的结论是“不应以轻罪处断”。关于前述问题B,牧野说的回答显然是“从重处罚”。除此之外,牧野说的另一特征在于,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案例中,轻罪的故意都是存在的,而不管行为人对于轻罪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
但问题在于,首先,在处理案例(Ⅰ)时,牧野说实际上认为“器物”与“人”是一致的,虽然没有砸坏跑车,但是打死了人,“人”也是“物”,所以可以构成损坏器物罪既遂。换言之,损坏器物罪与过失致死罪在抽象的层面上实现了符合。但如此一来,刑法条文区分犯罪类型的意义便丧失殆尽了,特别是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将难以维系,而“犯罪个别化机能”却是构成要件最应当发挥的机能之一。{10}其次,《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绝不仅仅是否定重罪的责任,而是对刑法谦抑主义与责任主义的贯彻。与之相对,牧野说的两个结论都认为在重罪要素不满足的状况下也可以作为重罪处断。这既不符合责任主义的要求,也违反了刑法谦抑主义。最后,如上所述,抽象的事实错误可以分为罪质完全不重合与罪质部分重合两种类型,而牧野先生在做论述时仅考虑了第一种类型。因此,牧野说在论述抽象的事实错误时仅涉及了刑罚的不均衡问题而忽视了罪质的重合程度问题。这种忽视致使牧野说只能作为一种原初学说存在,也正是这种忽视致使日本刑法学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跑偏现象:只考虑如何解决刑罚不均衡的问题而忽视了关于罪质重合程度的研究。
(二)草野说
草野豹一郎认为: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的事实时,构成轻罪的未遂与过失重罪的想象竞合,即使没有轻罪未遂的处罚规定也以轻罪的未遂处断。例如,在前述案例(Ⅰ)中,甲将构成损坏器物罪的未遂。再如,以遗弃患者(《日本刑法》第217条的遗弃罪,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遗弃了尸体(《日本刑法》第190条的遗弃尸体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将以遗弃罪的未遂处断。{11}93这是草野豹一郎著述中举到的事例,其理论构成类似于[2]前述案例(Ⅲ),如果改为案例(Ⅲ)的话,草野说的结论应当是,戊构成盗窃罪的未遂。由此可见,对于前述问题A,草野说的回答显然是“以轻罪论处”。
反之,以重罪的故意实现了轻罪的事实时,草野说认为构成重罪的未遂与过失轻罪的想象竞合,如果过失轻罪不受处罚,则定重罪的未遂,如果重罪的未遂不受处罚,则定故意轻罪。{11}93例如,在前述案例(Ⅱ)中,丙将构成故意杀人的未遂。再者,以伤害的故意损坏了器物时,将构成故意伤害未遂与过失损坏器物的想象竞合,因为故意伤害未遂与过失损坏器物都不可罚,所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刑罚不得超出故意损坏器物罪的规定限度。{11}93
草野说的特点在于:1.在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事实时,一律按照轻罪的未遂论处。但即使无轻罪未遂的处罚规定也要处罚的做法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2.当重罪的未遂不可罚时,草野说认为虽然轻罪是过失但也以故意论处。但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责任主义。总之,草野说解决了刑罚不均衡的问题,也部分涉及了罪质的重合程度问题,因而在结论上要比牧野说更为妥当,但这却是以牺牲罪刑法定主义与责任主义为代价的。
(三)合一评价说:植松说
植松正认为前述学说出现问题都是想象竞合惹的祸,因此,应当否定想象竞合,从一重罪论处即可。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的事实时,对轻罪的既遂与故意重罪进行合一评价,构成故意重罪,但为了不违反《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而仅在轻罪的刑罚幅度内处断。反之,以重罪的故意实现了轻罪的事实时,对重罪的未遂与故意轻罪进行合一评价,依照较重的罪名处断。{12}280以此为参照,在前述案例(Ⅰ)中,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但仅在损坏器物罪既遂的刑罚限度内处罚,与之相对,在前述案例(Ⅱ)中,首先对故意杀人的未遂与损坏器物进行合一评价,因为故意杀人罪的刑罚较重,所以丙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此外,在以保护责任人的故意实施遗弃(《日本刑法》第218条的保护责任人遗弃罪,刑罚为3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实际上遗弃了尸体时,对保护责任人遗弃的未遂与遗弃尸体的既遂进行合一评价,因为保护责任人遗弃的未遂不可罚,所以认定为遗弃尸体罪的既遂。
植松说的特点是对可能构成的犯罪进行合一评价,所以又被称为“合一评价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日高义博。{13}36这种“合一评价说”避免了在某种犯罪中必须得出构成轻罪或重罪、既遂或未遂的尴尬,从而不会出现轻罪未遂不可罚时也要处罚的弊端,在结论上更具灵活性。再者,将罪名与处断刑分别适用也是其特色之一。
不过,植松说的问题与宫本说相同,在处理以轻罪的故意实现重罪事实的事例时,植松说同样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与责任主义之嫌。此外,无重罪之故意时仍认定为重罪的做法也违反了《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因而饱受非议。{14}198而植松说更大的问题在于将前述学说的不当之处错误地归咎于想象竞合从而错过了真正的病灶:对罪质重合程度的忽视。更何况,植松说只是在表面上抛弃了想象竞合,而支配其得出结论的过程仍然是想象竞合的思维方式。
(四)可罚符合说:宫本·佐伯说
宫本英脩认为: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需要假定如下三种犯罪的成立。1.针对认识事实的未遂;2.针对发生事实的过失;3.针对发生事实的既遂。而后首先认定1与2的想象竞合关系,再认定3与1、2的法条竞合关系。{15}166例如,在前述案例(Ⅰ)中,首先认定损坏器物的未遂与过失致死的想象竞合,然后再与杀人的既遂实现法条竞合,最终认定为杀人罪的既遂,但因为有《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所以仅在损坏器物罪既遂的法定刑限度内处断。反之,在前述案例(Ⅱ)中,首先认定杀人未遂与过失损坏器物的想象竞合,然后再与损坏器物的既遂实现法条竞合,最终认定为杀人未遂。{15}143
宫本说可谓抽象符合说的最典型代表,针对一般规范意义上的故意概念,要求事实与认识的具体符合,而针对刑法上的构成可罚评价之标准的故意概念,则进行了抽象化处理。{4}265例如,在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事实的事例中,宫本说对故意做了极为抽象化的处理,将现实存在的损坏器物的故意与并不存在的杀人的故意同等看待了。此外,宫本说还从制定法通常不处罚过失与未遂的角度出发,以法条竞合的方式保证处罚的实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刑罚可罚的限度内认定犯罪的符合,故而被称为“可罚符合说”。
但是,宫本说的问题在于:在以轻罪的故意实现重罪事实的事例中,其结论可能会与制定法发生冲突。详言之,如果《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中的“不得以重罪处断”的含义是指“不得处以重罪之刑”的话,则宫本说没有问题,但如果其含义是指“不得认定为重罪也不得处以重罪之刑”的话,则宫本说的“认定为重罪但处以轻罪之刑”的做法将直接与制定法冲突了。而此处的“不得以重罪处断”显然是指既不能认定为重罪,也不得处以重罪之刑。此外,在行为人没有重罪的故意但却被认定为重罪既遂时,即使仅处以轻罪之刑,也是违反责任主义的。总之,宫本说在处理以轻罪的故意实现重罪事实的事例时,既避不开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批评,也有违反责任主义之嫌。
佐伯千仞也是可罚符合说的支持者,并且同样将故意概念一分为二。佐伯先生认为可罚符合说的理论前提在于严格区分“作为一般规范问题的故意”与“构成刑法中的可罚评价问题的故意”,前者称为“规范故意”,后者称为“可罚故意”。规范故意要求事实与观念具体地符合,在行为人有错误的限度内,他意图实现的故意行为的未遂与关于现实结果的过失之间应当实现想象竞合。与之相对,可罚故意则不要求事实与观念的具体符合,只要两者可罚地符合即可。{16}66-67法定符合说在解决打击错误的问题时实际上是采用了这种思路,但却将其局限在同一个构成要件之内,因而是不彻底的。为了彻底贯彻这种思路,需要做到如下三点:1.将故意犯的未遂与过失犯的既遂实现想象竞合;2.结合行为人意图实现某种犯罪的意思与他现实造成的过失结果,设想他对于现实发生的结果拥有可罚故意并因此设定故意犯罪的既遂;3.认定前两个问题存在法条竞合关系。{4}267根据佐伯说的思路,在前述案例(Ⅲ)中,首先认定为(普通)盗窃罪未遂,其次认定为过失盗窃枪支,最后认定为盗窃枪支罪既遂,但仅在(普通)盗窃罪既遂的刑罚限度内处断。反之,在前述案例(Ⅳ)中,首先认定为抢夺枪支罪的未遂,其次认定为过失抢夺,最后认定为(普通)抢夺罪既遂。
虽然同为“可罚符合说”,但宫本说与佐伯说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详言之,当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事实时,两种学说都认为构成重罪既遂但仅在轻罪的刑罚限度内处断。不过,当以重罪的故意实现了轻罪事实时,宫本说认为构成重罪未遂,但佐伯说认为构成轻罪既遂。比较而言,佐伯说的结论似乎更为妥当。
(五)抽象符合说的贡献:故意的二分化
抽象的事实错误之所以不好解决,是因为其中的故意跨越了不同的犯罪类型,由此引申出了故意论与归属论两个问题,前者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了使认定的犯罪类型中的故意成立,需要存在哪种程度上的认识,而后者的问题意识则在于:如何才能将具体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这种故意。归属论的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故意论问题的解决。而且,只有解决了故意论(以及归属论)的问题之后,才能探讨如何确立犯罪类型之共通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可罚符合说真正的贡献在于对故意的二分化处理,特别是其中的“可罚故意”堪称解决抽象事实错误的一把密匙。所谓“故意”,是指犯罪事实在行为人内心中的反映。{17}108易言之,故意是行为人对于侵害法益行为的认识与意欲。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需要行为人意欲实施的侵害法益行为与“现实上”[3]侵害法益的行为相一致[4]。这便是宫本·佐伯说中的“规范故意”。在不存在认识错误的犯罪中,只要观念与事实能够符合,便可以认定“规范故意”的成立。但在认识错误的犯罪中,因为两者不可能完全符合,所以需要利用“可罚故意”来解决问题。即从法规范的视角对于行为的可罚与否进行实质判断,此时要求的不是事实与观念的具体符合,而是实质性的可罚符合。换言之,实际上是对符合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抽象的、模糊的处理。为了保证这种抽象的、模糊的处理不会被滥用,则需要为可能符合的犯罪范围进行界定,而这个任务实际上是由法定符合说完成的,这便是罪质共通性的判断问题。
三、法定符合说的意义:罪质共通性的判断
抽象符合说的立论根据在于刑罚不均衡的问题。但实际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由于哪种学说造成的,而是由于立法中设置了不均衡的刑罚。将立法论的错误归咎于解释论显然是不合适的。{18}160此外,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如欲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则必须要对其故意内容做抽象化处理。但如果彻底抽象化处理故意的话,故意的实质内容将丧失殆尽,甚至导致犯罪论体系的崩溃。而抽象符合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突破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拘束,将无处罚规定的犯罪形态也作为犯罪处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与抽象符合说不同,法定符合说基本的思考方法在于如下两点:1.以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作为切入点。无论在具体的事实错误还是抽象的事实错误中,法定符合说都把握同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认定与现实发生的结果相对应的“个别的故意”。在具体的事实错误中,因为发生在同一个构成要件之内,所以法定符合说可以容易地得出“应当”的回答。与之相对,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因为故意跨越了两个构成要件,所以还需要从原本并不相同的两个构成要件中抽取出共通的要素。换言之,需要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探求犯罪类型的共通性,并以此来判断“个别的故意”与现实发生的结果之间是否符合。2.以此探讨构成要件的差别程度对于符合与否的影响。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之间自然存在差别,但差别的程度却迥然不同。差别较小的有杀人罪与同意杀人罪(《日本刑法》第202条),而差别较大的则有杀人罪与盗窃罪。前一种类型被称为基本的构成要件与派生的构成要件,因为重合程度较高,所以可以在轻罪的限度上认定符合。例如,以杀人罪的故意实施了同意杀人罪的行为时,因为在“实施了杀人行为”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可以在同意杀人罪的刑罚限度内处断。但差别程度大的犯罪则无法如此处理,法定符合说关于抽象的事实错误的争论实际上便是围绕这种类型展开的。由此可见,与抽象符合说不同,法定符合说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刑罚不均衡的问题转向了犯罪重合程度的问题。以此为契机,法定符合说发现了解决犯罪重合程度的另一把密匙——罪质共通性。不过,关于如何理解罪质共通性的问题,法定符合说内部出现了更为纷杂的争论。
(一)构成要件符合说
构成要件符合说认为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只有在同一个构成要件的范围内符合时才能认定为故意犯,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既然错误跨越了不同的构成要件,原则上不应认定为符合,而是分别成立未遂犯与过失犯。不过,如果不同的构成要件因为大小、轻重、包摄等而在实质上存在重合时,在其重合的限度内可以认定故意的符合。构成要件符合说又可以细分为两种:1.严格符合说,这种学说重视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认为应当对构成要件的重合进行严格解释,只有当刑罚法规相互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时才认定存在重合。{19}265{20}116如此一来,能够认定为重合的构成要件恐怕只有寥寥几种了。例如,普通杀人与同意杀人,普通遗弃与加重遗弃,侵占与业务上侵占。{21}135以此为标准,在罪质部分重合的案件例如前述案例(Ⅲ)、(Ⅳ)中,可以认定存在符合。除此之外,便不可能有符合了。这种严格的解释使符合的存在空间极度压缩,抽象的事实错误也丧失了绝大多数阵地,因而为多数学者所不喜。{22}9762.形式符合说,该说主张对构成要件的重合进行形式解释。例如,在共犯错误的案件中,在盗窃与抢劫,恐吓与抢劫,伤害与杀人之间,都可以在前者的限度上认定存在重合。{23}426{24}123{25}222与严格符合说相比,形式符合说扩大了构成要件的重合范围,即使罪名之间没有共通性,但只要可以认可构成要件之间的大小包摄关系,便可以认为构成符合。但问题在于,上述构成要件实际上是无法在形式上符合的。例如,恐吓罪是基于受害人的意思对财物或利益进行了转移,而抢劫罪却是违背受害人的意思进行了财物或利益的转移。两罪之间应当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非重合关系。
(二)实质符合说
实质符合说更进一步,主要对构成要件的符合做出了更为实质的判断,具体的判断标准则因人而异。例如,大塚仁教授的“法益·行为共通性说”主张以法益以及行为的共通性作为认定标准,只要这种共通的类型符合社会通常观念即可。{26}197{27}61因此,伪造公文书罪(《日本刑法》第155条)与伪造虚假公文书罪(《日本刑法》第156条)之间也可以符合。其理由在于,构成要件是侵害法益行为的类型化,此外,构成要件行为是依据社会通常观念有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的行为。因此,认定符合时,不仅需要认识的内容与发生的事实在形式上实现构成要件的重合,还需要以保护法益的共通性以及构成要件行为的共通性为基础,依据社会通常观念来认定构成要件的重合。{28}177而平野龙一教授则主张以“构成要件内容的包括性或外延的包摄性”作为认定标准。{29}178内容包括性的例子有杀人与同意杀人,杀人与伤害,盗窃与侵占脱离占有物,而外延的包摄性则是指在同一个构成要件内做择一式规定的情形,例如,使用印章伪造公文书与使用签名伪造公文书,同意杀人与帮助自杀。此外,在立法技术上分别规定于不同条文中的情形也属于外延包摄性。例如,伪造公文书罪与伪造虚假公文书罪,持有海洛因罪(《日本麻醉药品及向精神药品取缔法》第66条第3款规定的持有麻醉药品罪,刑罚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与持有冰毒罪(《日本冰毒取缔法》第41条之2第3款规定的持有冰毒罪,刑罚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也可以符合。法益与行为的共通性确实是罪质共通性的关键要素,但以社会通常观念作为认定标准的做法却有过于宽泛之嫌。此外,平野先生将规定于不同法条中的罪名也视为外延包摄性的做法显然扩大了其范围。因此,实质符合说的认定标准颇具参考意义,但标准的模糊性导致了符合范围的扩大化。
(三)罪质符合说
罪质符合说主张以法益和犯罪方法为标准,考虑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来认定符合。因此,即使构成要件并不符合,但仍然可以在罪质同一的范围内认定故意的成立。此时的“法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概念,而是一般人都会如此理解的概念。故而,可以凭借这种法益概念为罪质的符合性寻求根据。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罪质符合说认定的符合范围更广,例如,遗弃尸体罪与普通遗弃罪之间也存在符合。{30}199其理由在于,虽然两罪的构成要件不同,保护法益亦不同,但从社会生活实践上来看,当被遗弃人究竟是刚刚去世还是弥留之际的问题并不明确时,在遗弃人有“遗弃的意思”这一点上,无论针对尸体还是针对活人都可以成立,因此,便可以在罪质同一的范围内认定故意的成立。但是,关于“罪质”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判断的问题,罪质符合说语焉不详。{4}270此外,法益对于认定犯罪的意义重大,因而模糊不得。仍以遗弃尸体与普通遗弃为例,前者的法益是公众对死者的虔敬感情,后者的法益是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权,两者截然不同,如果这样都可以认定为符合的话,那么法益的存在价值与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都将是镜花水月了。
(四)不法·责任符合说
不法·责任符合说认为构成要件的形式性符合不过是表象而已,其实质在于构成要件的不法、责任内容的符合。该说认为:实质符合说实质性地扩张了构成要件,导致构成要件概念的松弛,从而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为了肯定故意的成立,即使没有关于构成要件符合事实的认识,但只要有关于组成构成要件之内容的不法、责任的认识即可。因此,即使认识事实与实现事实在构成要件的范围上并不符合,但只要在各个构成要件的不法、责任内容上符合即可。{31}该学说的特点在于否认了故意与构成要件的关联性,并以此为基础对故意概念本身进行了调整,但其结论与实质符合说没有差别。此外,既然需要有关于组成构成要件之内容的不法、责任的认识,那么至少需要有关于构成要件符合事实的认识,若非如此,则认识的内容便不可能成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外部)事实的线索,也就沦为了可以随意设定的模糊的要素了。{32}122
(五)法益符合说
法益符合说认为,在为了保护同一法益而择一式地规定构成要件时,只要构成要件在侵害法益或侵害法益的危险方面存在重合部分即可。{33}269但这种过于宽泛的的认定方法为学界所不喜,因而属于极少数说。
(六)法定符合说的贡献:罪质共通性的认定思路
法定符合说的着眼点在于犯罪的重合程度,特别是在形式上似乎不重合的犯罪中,能否抽出共通要素来认定重合问题才是解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法定符合说认为核心问题在于罪质的共通性,其分支学说众说纷纭的原因正是在于对罪质共通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法定符合说仍然做出了重大贡献:1.对于抽象符合说以刑罚不均衡作为立论基础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指出刑罚不均衡的问题并非抽象的事实错误论即解释论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应从立法论上加以解决。{34}1232.提出了解决罪质重合程度的要义——罪质共通性。关于罪质共通性的判断,既然构成要件之间的实质符合应当发生于不法类型性一致时,故而,至少需要在“法益侵害或危险化(结果无价值)”与“行为状况(行为无价值)”这两个层面上存在重合。换言之,只有当法益与行为这两个要素都存在共通的可能性时,才能认定为符合。在通行的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是不法(违法行为)类型,因此,构成要件之间的实质符合应当发生于不法类型性一致时。故而,至少需要在“法益侵害或危险化(结果无价值)”与“行为状况(行为无价值)”这两个层面上存在重合。{35}133
四、罪质共通性说的判断要素、内涵及适用
笔者认为,解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关键在于对罪质重合(即共通性)程度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则取决于“可罚故意”与“罪质共通性”两项要素。在前述学说的基础上,笔者以这两项要素为依托,提出判断罪质共通性程度的新思路,并命名为“罪质共通性说”。本部分将首先介绍这两项要素的具体内容及机能,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罪质共通性说的内涵及适用。
(一)罪质重合的判断要素
1.可罚故意
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对于事实的认识,究论之,意指行为人对于事实含义的认知。此处的含义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非刑罚规范的概念。有时,即使行为人清楚地知道法规范概念,也并不一定会有刑法规范指向的故意。{36}158例如,可卡因的化学名称为苯甲基芽子碱,甲将一包可卡因交给乙保管,并告诉乙“这是苯甲基芽子碱”,但乙却并不知道这就是可卡因而仅仅以为是普通药品。此时,虽然乙在客观上持有毒品,但却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因在于乙欠缺持有毒品罪的故意。刑罚规范是裁判规范,将其翻译为普通人可以了解的规范后才是行为规范。因此,当行为人根据翻译的语言可以认识到构成要件的含义内容时,故意才成立。正因此,即使两种犯罪在构成要件要素即裁判规范的层面上存在排他关系,但只要满足两罪之故意的认识内容在行为规范的层面上可以重合,便至少可以在轻罪的限度上认定故意的存在。
在没有错误的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行为规范有清楚的认识[5],“规范故意”与“可罚故意”同样成立。而在有错误的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行为规范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规范故意”难以成立,但“可罚故意”却是有可能成立的。如果“可罚故意”能够成立,便可以在“可罚故意”指向的犯罪类型上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详言之,仍以乙持有“苯甲基芽子碱”的案例为例,如果乙完全不知道“苯甲基芽子碱”是违禁药品,则乙既无“规范故意”,也无“可罚故意”,不会成为刑罚规范的评价对象。如果乙认为“苯甲基芽子碱”是海洛因的话,那么,便至少可以从“禁止持有毒品”这一行为规范的视角对乙的行为进行评价,此时,虽然乙对于所持有的毒品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但并不影响乙关于“我持有了法律禁止持有的毒品”这一认识的成立。既然存在这种认识,刑罚规范便具备了介入的可能性,这便是“可罚故意”的认定思路。即,当实现A罪的意思与实现B罪的意思相重合,以实现A罪的意思客观上实现了B罪的事实时,在侵害了B罪的行为规范的限度上,可以肯定故意的成立。
2.罪质共通性
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只有在罪质具备共通性的犯罪之间,才可能出现符合问题。如果不存在罪质共通性,则不应将跨越两个构成要件的错误做一体评价,否则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以盗窃罪与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为例。在前述案例(Ⅲ)中,戊在主观上是普通盗窃的故意,但客观上盗窃了枪支。因为枪支可以被评价为财物,所以两罪具有罪质的共通性。详言之,在行为的共通性方面,普通盗窃与盗窃枪支在性质上同为盗窃行为,都是违反占有人的意思而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两者具备共通性。而在保护法益方面,普通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物所有权及其他本权,以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回复应有状态)的占有。{1}838与之相对,盗窃枪支罪被归类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但并不影响其次要保护法益是关于枪支的占有状态。因此,在都以枪支(财物)的占有状态作为保护法益这一点上,两罪是具备共通性的。既然在行为与法益方面都具备共通性。那么,两罪便具备罪质共通性。在前述案例(Ⅲ)中,当戊以普通盗窃的故意客观上盗窃了枪支时,可以在(普通)盗窃罪的限度内处断。同理,(普通)抢夺罪与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之间也具备罪质共通性。因此,在上述案例(Ⅳ)中,当庚以抢夺枪支的故意客观上抢夺了钱时,可以在(普通)抢夺罪的限度内处断。这是罪质共通性的典型,上述犯罪不仅在实质上存在共通性,而且在形式上也存在此罪包摄彼罪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犯罪类型。
除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犯罪类型之外,一般犯罪与兜底犯罪之间也可以实现抽象的符合,此时需要借助“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所谓“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某些不是为了给违法性、有责性设定根据,而只是为了区分相关犯罪(包括同一犯罪的不同处罚标准)的界限的要素。{37}255例如我国《刑法》第270条第2款中的“遗忘物、埋藏物”。该类要素的功能在于对罪质共通的犯罪提供区分标准,承认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有利于减少具体犯罪之间的对立关系、排他关系,增加具体犯罪之间的位阶关系、包容关系,进而使具体犯罪之间更为协调,从而实现刑法的正义性。{37}264例如,甲误认为乙放在公园长椅上的财物是遗忘物而顺手牵羊时,为了将甲的行为认定为侵占遗忘物罪的既遂,需要提供合理的解释。由于侵占遗忘物罪中的“遗忘物”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仅起到将本罪与盗窃罪、普通侵占罪区分开来的作用。所以,侵占遗忘物罪是“领得罪”中最简单的类型,其对象是“他人的财物”。本罪的成立,既不要求盗窃罪的夺取(侵害占有),也不要求诈骗罪的由受害人交付财物(处分行为),更不要求侵占委托物罪的委托关系。作为侵害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犯罪,本罪发挥的是在由于某些理由无法构成其他犯罪时可以认定为本罪的兜底作用。{38}269因此,在上述案件中,虽然甲并没有盗窃的故意,但由于他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财物,主观上也具有侵占的意思,因而可以认定为侵占遗忘物罪,而无需甲对于该财物究竟是否是遗忘物有确切的认识。换言之,盗窃罪与侵占遗忘物罪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包摄关系,但从实际上来看,两罪在罪质上具备共通性,因而可以构成抽象的符合。
(二)“罪质共通性说”的内涵
如上所述,在抽象符合说中,牧野说、草野说以及植松说实际上都是以见招拆招的方式对具体罪名之间的符合问题作出了解答,因而难逃欠缺系统性的批判。可罚符合说为了避免这种不足而提高了理论程度,由此得出了故意二分法的思路。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与客观实现的犯罪事实之间跨越了不同的犯罪类型,因此,如欲将客观实现的犯罪事实归责于行为人的故意,则应当探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可罚的符合性,而无法要求两者之间具备具体的符合性。这便是可罚故意与规范故意的分离,而这正是抽象符合得以被认定的前提,也正是抽象符合说的真正贡献。当然了,如果仅以可罚故意的成立作为标准,那么可以认定为抽象符合的犯罪类型将大量存在,例如,在杀人与损坏财物、侮辱尸体与强奸之间,可罚故意都是成立的。因此,还需要追加其他标准进行限制。换言之,利用行为与法益的共通性来限制抽象符合的成立范围,此时要求的是行为与法益都具备共通性,而并非一项具备即可。因此,罪质共通性说是以可罚故意为抽象符合的成立架设桥梁,并且以行为与法益的共通性为其划定范围。
罪质共通性说的理论依据在于可罚故意与罪质(行为与法益)共通性,因此,其直接理论渊源是可罚符合说中的佐伯说与实质符合说中的大塚说,但与两者又有明显不同。详言之,当以轻罪的故意实现了重罪的事实时,佐伯说认为构成重罪既遂但仅在轻罪的刑罚限度内处断,而罪质共通性说认为构成轻罪的既遂。例如,在前述案例(Ⅲ)中,依照佐伯说,将构成盗窃枪支罪既遂,但仅在(普通)盗窃罪的刑罚限度内处罚。与之相对,罪质共通性说认为构成(普通)盗窃罪既遂。当以重罪的故意实现了轻罪的事实时,罪质共通性说与佐伯说都认为构成轻罪的既遂。例如,在前述案例(Ⅳ)中,两种学说都认为构成(普通)抢夺罪既遂。不过,佐伯说并未分析罪质不共通时如何判断的问题,而罪质共通性说则深入了一步。例如,以强奸的故意实际上侮辱了尸体时,按照佐伯说的思维方式,应该会得出构成侮辱尸体罪既遂的结论,与之相对,罪质共通性说则会以两罪的罪质不共通为理由,得出构成强奸罪未遂与过失侮辱尸体(无罪)的结论。这便是罪质共通性说与佐伯说之间的差别。此外,罪质共通性说与大塚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塚说以行为与法益的共通性作为标准,认为这种共通只要契合通常的社会观念就可以认定为符合。与之相对,罪质共通性说则认为行为与法益的共通性并不必然得出构成符合的结论,并且,这种共通应当契合法规范观念而非社会观念。即,在作符合与否的判断时,应当将法规范理解为裁判规范而非行为规范,因为此时做出判断的是法官等专业人员而非普通民众。再者,大塚教授在论著中列举了将冰毒误认为是可卡因而持有的案例,并且没有反对最高院的判决结论(构成持有麻醉药品(可卡因)罪既遂)。与之相对,根据罪质共通性说,此时应当构成持有麻醉药品(可卡因)罪的未遂与过失持有冰毒(不可罚)。
虽然同样都使用了“罪质”一词,但罪质共通性说与罪质符合说截然不同。首先,罪质共通性说以法益与行为的共通性作为标准,而罪质符合说则以法益与犯罪方法的共通性作为标准。再者,罪质共通性说中的法益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概念,而罪质符合说中法益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概念。例如,罪质符合说认为遗弃尸体罪与(普通)遗弃罪之间可以符合,而罪质共通性说则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原因在于两罪的法益截然不同。
(三)罪质共通性说的适用
中国刑法典中并不存在类似于《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因此,在法教义学方面,不会出现日本刑法学面对该条款时的理论纠结。反过来说,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缺乏,使中国刑法学关于错误论的关注度略显不足。但是,笔者认为,无论立法中是否存在类似规定,从严格贯彻责任主义的要求出发,在行为人欠缺实施重罪的故意但客观上实现了重罪事实时,理所当然地不能以重罪论处。此外,当行为人以实施重罪的故意但客观上仅实现了轻罪事实时,关于能否一概认定为重罪的问题,也存在商讨的余地,这便是抽象的事实错误的理论意义。
在抽象的事实错误中,符合不可能发生在罪质不重合的犯罪之间。例如,在前述案例(Ⅰ)、(Ⅱ)中,便只能对两个犯罪分别进行评价了。在案例(Ⅰ)中,甲将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的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犯。因为前者不可罚,所以仅需认定为后者。在前述案例(Ⅱ)中,丙将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与过失损坏财物,因为后者不可罚,所以仅需认定为前者。不可能存在符合的原因在于:具备罪质共通性的犯罪类型必须在行为与保护法益上都具备共通性。因此,保护法益不具备共通性的犯罪之间不会出现符合。例如,盗窃尸体罪与盗窃罪之间不会符合,原因在于,前者的法益是公众对于尸体的虔敬感情,而后者的法益是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因此,当行为人以盗窃的故意实际上盗窃了尸体时,应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与过失盗窃尸体,因为过失盗窃尸体不可罚,所以仅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此时,不可能以尸体是亲属的财产为理由认为盗窃尸体也侵犯了财产权,也不能以尸体与活人只差一口气为理由认为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同样的道理,侮辱尸体罪与遗弃罪之间也不会构成符合,将尸体遗弃在公共场合时可以构成侮辱尸体罪,如果行为人以这种故意实施遗弃但被遗弃人一息尚存的话,应当认定为侮辱尸体罪的未遂与过失遗弃,因为过失遗弃不可罚,所以仅认定为侮辱尸体罪的未遂。其理由在于,既然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那么,法益侵害便是其内核,故而不可能无视侵害法益的共通性来认定构成要件的符合。{28}178以此类推,侮辱尸体罪与强奸罪之间也不会符合。与之相对,在罪质存在重合部分的犯罪中,则可以依据罪质共通性认定符合的成立。铃木茂嗣教授指出: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看,即为“包摄型”犯罪类型,又可以分为“形式包摄型”与“实质包摄型”。前者是指法条在规定形式上采用了包摄方式的犯罪类型,后者是指从立法宗旨上来看可以包摄的犯罪类型。{39}110在罪质共通性说的标准中,前者是指形式上包摄并且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而后者是指形式上不包摄但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详情如下:
1.在中国刑法中,形式上包摄并且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包括: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盗窃罪、抢夺罪与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以及《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的金融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其他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为例,从可罚故意的角度来看,行为人以生产假药的故意客观上实现了生产伪劣产品的事实,因此,行为人的意图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可罚的符合性。即,在不应当生产伪劣商品但却生产的层面上,无论生产假药所要求的可罚故意还是生产伪劣产品所要求的可罚故意都是存在的,两者具备一致性。此外,从行为上来看,两者在生产行为上具备一致性。从法益上来看,生产假药罪侵犯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同时还侵犯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益,生产伪劣产品罪侵犯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同时还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药品是一种特殊产品,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权是合法权益的一种。因此,两罪在保护法益上也存在重合部分。所以,当行为人误认为阿胶是药品,以生产假药的故意生产了假阿胶时,即使这种假阿胶无毒、无害并且不会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只要销售金额达到了5万元以上,便可以作为轻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进行处罚。
2.形式上不包摄但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此时需要借助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具备这种特征的犯罪有如下几种:盗窃罪、侵占罪与侵占遗忘物、埋藏物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非法出售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其他的走私类犯罪。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本法第151条、第152条、第347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才成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当行为人误将贵重金属认为是普通金属而走私时,如欲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最好的途径便是认为《刑法》第153条中的“走私本法第151条、第152条、第347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表述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从而将第153条视为关于走私犯罪的兜底条款,并由此得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既遂的结论。再如,以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非法出售发票罪为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但实际上非法出售的仅仅是普通发票时,可以认定为非法出售发票罪的既遂。反之,当行为人主观上是非法出售普通发票,但实际上非法出售的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时,由于行为人欠缺实施重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的故意,所以也应当认定为非法出售发票罪的既遂。
结语
综上所述,能够认定构成符合的抽象的事实错误类型是不太多见的。从罪刑法定主义与责任主义的要求出发,构成要件存在的意义便是为不同的犯罪类型划定认定范围,这便是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与故意(过失)规制机能。{40}因此,当错误跨越了不同的构成要件时,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认定符合的成立。关于认定的标准则取决于“可罚故意”与“罪质共通性”两项要素。可罚故意是指从法规范的视角对于行为人侵害法益的观念进行的可罚评价,并且,可罚故意的判断需以规范故意的共通为前提。在罪质完全相异的犯罪之间,例如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之间,规范故意都不可能共通,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可罚故意的存在与否。而在罪质具备共通性的犯罪之间,例如盗窃罪与盗窃枪支罪、遗弃罪与(以遗弃方式)侮辱尸体罪之间,因为规范故意是共通的,便可以对可罚故意之成否进行评价了。在可罚故意成立的情况下,只有在行为与法益都具备共通性的犯罪之间才可能认定符合的成立。例如,遗弃罪与侮辱尸体罪便因为法益有别而无法符合。如此一来,可以认定存在符合的犯罪类型应当是行为、法益两者之间都存在共通性的犯罪。这种犯罪类型又分为:形式上包摄并且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形式上不包摄但实质上共通的犯罪类型。除此之外的犯罪之间如果出现了错误的话,则不应当认定为符合,而应分别作出判断了。
【注释】
[1]牧野英一实际上是错误论的创始人,“具体符合说”、“法定符合说”、“抽象符合说”这三个术语皆为牧野英一原创。在其名著《刑法改正的诸问题》中,牧野不无得意地指出:“所谓符合问题是指,当行为人的设想与实际发生的犯罪事实并不一致时,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忽视这种不一致的问题。换言之,这是指犯意与事实在哪些情形中可以在法律上符合,即,犯罪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哪种情形中可以具备的问题。我称之为‘符合的问题’,并将该符合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具体符合,第二种为法定符合,第三种为抽象符合。上述术语系我本人因个人喜好所用,并非译语。实际上,关于上述三种符合的区别,在欧洲学者中也并未明确地论及。但我本人认为理应进行充分的考量。”参见〔日〕牧野英一:《刑法改正的诸问题》,良书普及会1934年版,第214页。
[2]实际上,以普通盗窃的故意但客观上盗窃了枪支的案例与以遗弃的故意但客观上遗弃了尸体的案例之间仍有不同。在前者中,普通盗窃与盗窃枪支在罪质上确实存在重合部分,而在后者中,普通遗弃与遗弃尸体在行为类型上是共通的,但在保护法益方面则有差别。关于普通遗弃与遗弃尸体之间能否符合的问题,在日本学界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因此,此处只能暂且表述为“类似于”了。
[3]当然,在错误论的情况中,这种“现实上”仅仅是观念性的。
[4]实际上也不要求完全一致,例如在错误论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便不完全一致。
[5]不需要彻底清楚,但至少能保证刑法规范可以做出合法与否的判断。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日〕松宫孝明.刑事立法与犯罪体系〔M〕.东京:成文堂,2003.
{3}〔日〕浅田和茂.刑法总论(补正版)〔M〕.东京:成文堂,2007.
{4}〔日〕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第3版)〔M〕.东京:成文堂,2013.
{5}〔日〕牧野英一.刑法改正的诸问题〔M〕.东京:良书普及会,1934.
{6}〔日〕川端博.错误论的诸相〔M〕.东京:成文堂,1996.
{7}〔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改订版)〔M〕.东京:有斐阁,1947.
{8}〔日〕小野清一郎.刑法中的责任原理即所谓“责任说”〔J〕.法学家,1966,(338):30—38.
{9}〔日〕牧野英一.刑法总论下卷(On Demand版)〔M〕.东京:有斐阁,2001.
{10}〔日〕松宫孝明.构成要件的概念与机能〔J〕.刑法论丛,2014,(2):33—53.
{11}〔日〕草野豹一郎.刑法要论〔M〕.东京:有斐阁,1956.
{12}〔日〕植松正.再订刑法概论Ⅰ总论〔M〕.东京:劲草书房,1974.
{13}〔日〕日高义博.刑法中错误论的新展开〔M〕.东京:成文堂,1991.
{14}〔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2版)〔M〕.东京:成文堂,2013.
{15}〔日〕宫本英脩.刑法大纲〔M〕.东京:弘文堂,1935.
{16}〔日〕佐伯千仞.刑法的理论与体系〔M〕.东京:信山社,2014.
{17}〔日〕高山佳奈子.故意与违法性意识〔M〕.东京:有斐阁,1999.
{18}〔日〕小野清一郎.新订刑法讲义总论〔M〕.东京:有斐阁,1948.
{19}〔日〕香川达夫.刑法讲义(总论)(第3版)〔M〕.东京:成文堂,1995.
{20}〔日〕大越义久.刑法总论(第3版)〔M〕.东京:有斐阁,2001.
{21}〔日〕佐久间修.刑法总论〔M〕.东京:成文堂,2009.
{22}〔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下Ⅰ)〔M〕.东京:有斐阁,2002.
{23}〔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第3版)〔M〕.东京:创文社,1990.
{24}〔日〕福田平.全订刑法总论(第4版)〔M〕.东京:成文堂,2004.
{25}〔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M〕.东京:有斐阁,2007.
{26}〔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4版)〔M〕.东京:有斐阁,2008.
{27}〔日〕大塚仁.刑法的焦点一:错误〔M〕.东京:有斐阁,1984.
{28}〔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4版)〔M〕.东京:成文堂,2012.
{29}〔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M〕.东京:有斐阁,1972.
{30}〔日〕西原春夫.刑法总论〔M〕.东京:成文堂,1977.
{31}〔日〕町野朔.论法定符合(下)〔J〕.警察研究,1983,54(5):3—27.
{32}〔日〕川端博.事实错误的理论〔M〕.东京:成文堂,2007.
{33}〔日〕林干人.刑法总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
{34}〔日〕福田平.全订刑法总论(第5版)〔M〕.东京:有斐阁,2011.
{35}〔日〕伊东研佑.刑法讲义总论〔M〕.东京:日本评论社,2010.
{36}〔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M〕.东京:有斐阁,2008.
{37}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8}〔日〕松宫孝明.刑法各论讲义(第3版)〔M〕.东京:成文堂,2013.
{39}〔日〕铃木茂嗣.刑法总论(第2版)〔M〕.东京:成文堂,2011.
{40}张小宁.犯罪论体系与构成要件的机能〔J〕.刑法论丛,2014,(2):54—68.
【作者简介】张小宁,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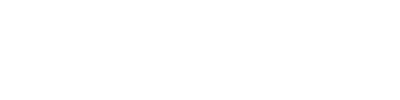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