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坤
共犯具有对正犯的从属性,这是二元区分制理论的立足点。而正犯包括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因此,共犯具有对直接正犯或间接正犯的从属性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在既存在直接正犯又存在间接正犯即所谓“正犯后的正犯”[1]的场合,共犯究竟是对直接正犯还是间接正犯具有从属性呢?如甲、乙得知B在丙的帮助下准备于特定的夜晚埋伏在A经常散步的偏僻处将A射杀。于是甲教唆A利用B的行为将仇人C杀死,乙顺手把自己的手机给了A,而A产生杀死C的故意后,使用乙的手机给C发了假消息(以C恋人的名义),试图将其引诱至该场所,但C因为临时有事而未能出现在现场,结果B未能实施射杀行为。[2]本案中,毫无争议的是丙作为直接正犯B的帮助犯,对直接正犯B具有从属性;问题是作为共犯的甲、乙究竟是对间接正犯A还是对直接正犯B具有从属性?如果二者对直接正犯B具有从属性,则三者同属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犯。如果甲对所教唆的、乙对所帮助的间接正犯A具有从属性,则需要判断A是否“实行着手”:是,则三者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犯;否,则三者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预备犯。本文认为间接正犯是拟制的正犯,仍然具有对幕前行为人即直接实行人的从属性;因为间接正犯具有对直接实行人的从属性,所以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标准只能采取“被利用者时说”。
一、溯本:间接正犯是拟制的正犯
犯罪参与中,间接正犯与共犯具有相同的侵害法益的行为结构,二者都是通过直接行为人所实施的构成要件行为侵害法益的,因此从自然的因果流程来看,根本无法从形式上将二者加以区分。而从间接正犯概念的来源看,间接正犯其实是从教唆犯中分立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作为教唆犯的替补角色出现的,因此,在利用行为表现为“唆使”的时候,究竟是成立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很难区分。如行为人甲明知乙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而唆使其盗窃的,理论上一般认为,甲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若甲以为乙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实际上甲已达刑事责任年龄而唆使其犯罪的,与前者相比,不仅在客观上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完全一样,都是利用乙盗窃的“唆使”行为,而且主观上的故意内容也完全一样,都是“利用乙盗窃的”意思,然而,此时甲究竟是成立盗窃罪的教唆犯还是间接正犯就会产生争议。
究竟该如何区分间接正犯与共犯呢?“为了明确间接正犯的概念,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去进行考察:其一,所谓这种正犯的积极的方面(正犯性);其二,所谓不是共犯的消极方面(非共犯性)。”[3]消极地论证间接正犯的非共犯性,就是要把在客观上形同共犯的行为排除出共犯的范畴,将其纳入正犯的规制之中,从而进一步论证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而积极地论证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就是要论证间接正犯如同直接正犯一样实现了构成要件。从而所有的关于间接正犯的理论争点,如间接正犯的本质、间接正犯的着手、间接正犯的错误等重要问题,无不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直接相关。
间接正犯之所以被称为间接正犯,是因为幕后正犯之前有直接实现构成要件之人作为幕后正犯的行为中介。“作为行为媒介的第三人”就是直接行为人,没有“行为媒介的第三人”的直接行为人,间接正犯就无从谈起。因此,如何理解作为“行为媒介的第三人”,就成为间接正犯理论中的一大障碍。
为清除这一障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淡化“行为媒介入”的地位或作用,从而将间接正犯视为与直接正犯一样,都是(亲自或通过他人)实现构成要件之人。从行为人利用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者犯罪的场合中,理论上发现了采取严格从属性;[4]说所存在的漏洞,发现“行为媒介入”其实只是犯罪的工具。于是,“工具理论”认为,“实行行为并不必然是行为人亲自实现构成要件。如同使用器具、驱使动物作为工具一样,也可以是把人作为工具”。[5]因此,按照“工具理论”,亲自实现构成要件的,是直接正犯,而把人作为工具犯罪的,就是间接正犯。间接正犯并不是正犯之外的特殊形态,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都是刑法所规制的正犯。而为了论证后行为人的行为的正犯性,就必须把重点放到“工具适格”的判断上,即在具体的个案中,必须论证被利用人仅仅是单纯的被利用的工具。然而,这种朴素的、直观的、比喻式的判断标准并不具有明确性,只要是人,就必定有自己的判断力,即使是无责任能力人,也有自己的意识与思维活动;对于实际上具有辨认行为的性质、并基于辨认能力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未成年人而言,仅仅因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刑法上认为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就更难说他们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人其实不能被作为工具看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不法行为的,同样需要在刑法上作出“客观不法”的谴责性评价,虽然因为没有责任能力阻却责任而不能科处刑罚,但是却可以对其予以保安处分等处罚。而且,如果把被利用人局限在被利用的“工具”上,会缩小间接正犯成立的范围,这一点,从不断扩大的间接正犯的类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日本刑法学界以实行行为性为标准的通说即“实行行为性说”则认为,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质的实体,存在于与直接正犯没有差异的实行行为性之中,亦即,就背后的利用人的行为而言,主观上具备实现犯罪的意思,客观上,被利用者的行为实现了一定犯罪(即达到了法益侵害、威胁的现实的危险性)。[6]所谓正犯,原本应解释为自己亲手实行具有实现构成要件现实危险性行为之人即直接正犯,由于间接正犯实行的是具有间接使构成要件的实现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因此被视为正犯进行处理。按照实行行为性说的观点,是通过对利用行为进行实质地规范评价,获得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质的。由于通说认为,构成要件行为即实行行为是在客观上具有法益侵害或危险的行为,因此,通说也从这一点上实质地解释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质。“但是,‘实行行为’概念本身内容含糊、范围宽泛,对其有多种理解,仅仅根据‘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是正犯,而为实施实行行为提供方便的是共犯’的形式标准,并不能将正犯和共犯区别开来。”[7]
很显然,“工具说”与“实行行为性说”尽量忽视被利用人所具有的人的属性,“工具说”强调“被利用人是工具”,而“实行行为性说”则把“被利用人的行为”作为判断“利用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或危险的所谓实行行为性质的工具。因此,这两种学说都是把利用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
然而,即使通过实质解释的方法把后行为人的利用行为解释为实行行为,也无法绕开对被利用行为的评价,即被利用行为才是具有法益侵害或危险的行为。因此,大谷实教授一方面坚持“工具说”的基本观点,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利用他人为工具犯罪的意思,客观上有把他人作为工具实现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强调,“不要将利用行为和被利用行为分开,分别进行刑法评价,而应该根据间接正犯的意思,将被利用行为和利用行为统一,视为一体,作为利用人(行为人)的实行行为进行评价。因此,在被利用人方面,具有按照行为人的意思进行活动的规范障碍时,由于被利用人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下,不能被看做利用人的实行行为,因此,在该种场合下,就不是间接正犯,原则上成立共犯,特别是教唆犯”。[8]理论上将这种观点称为“规范障碍说”。“规范障碍说”有两个特点,一是给予了对被利用人作为人的属性的重视,二是将利用行为与被利用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评价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
而“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则认为,对犯罪实施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人物或核心角色,对犯罪事实处于支配性地位者,就是正犯。在直接正犯中,实施者通过采取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而获得对犯罪事实的控制,是行为支配;间接正犯则通过利用他人〔构成要件行为中介者(Tatmittler)〕并将其加以工具化(用作“工具”)而间接(作为“幕后者”)支配事件过程的方式,让他人为自己的目标出力,从而实现不法之构成要件,是意志支配;而共同正犯则是作为功能性犯罪事实支配。[9]
上述各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强调间接正犯所实施的行为的重要性,“工具说”认为,后行为人的行为就是把人作为工具的行为,被利用人是工具,当然就确定了后行为人的正犯地位;“实行行为性说”干脆说“利用行为与直接正犯的行为一样,都是实行行为”;“规范障碍说”则说,“利用行为是实行行为,但是要结合被利用人的行为进行判断”;“犯罪事实支配说”则从犯罪事实支配、控制了犯罪过程、犯罪的核心角色这一点上找到了间接正犯与直接行为人的相同点,从而将没有直接实施构成要件的间接行为人也纳入正犯的范畴之类。这种寻找幕后犯罪参与人与直接行为人的相同性,并将其视为直接行为人一样处理的拟制过程,一方面是作为间接正犯的积极方面即正犯性的论证过程,同时又是不断压缩共犯的成立范围,将其作为正犯处理的拟制过程。
间接正犯本来是教唆犯的替补角色,但是理论上不断将其予以扩张解释。在类型化方面,从利用无责任能力者的单纯的工具,到有责任能力者也可以是间接正犯利用的对象;从利用有故意的工具,到利用过失的行为;从利用第三者的行为,到强制被害人自己实施法益侵害行为;从利用违法有责行为,到利用违法行为,再到利用构成要件行为,甚至利用合法行为……直到间接正犯理论发展到间接正犯只是一种犯罪事实的描述,而刑法所关心的仅仅在于幕后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是否具有事实上的控制。这种间接正犯适用范围扩大的过程,也正是共犯不断被拟制为(间接)正犯的过程。
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理论论证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都无法否定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本质上所具有的“拟制性”特点。这一点,早在间接正犯的滥觞之时,李斯特诸学者就已经指出来了。[10]
二、还原:间接正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
在二元区分体系下,间接正犯与直接行为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独立抑或从属?
(一)独立性说的疑问
对此,学界有观点指出,间接正犯是独立的正犯,它对于被利用者没有任何从属性,只有利用行为才是间接正犯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至于被利用者的行为,不过是利用行为与结果之中间现象而已。[11]这其实正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既然间接正犯与直接正犯都是正犯,那么从形式上看,二者之间自然就是彼此独立的了,自无从属性可言。这意味着间接正犯的违法性来自于“利用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违法性。
但是,通说的观点至少存在两个疑问:
(1)从间接正犯的理论由来看,间接正犯系从教唆犯中分离出来的,在很多场合下,唆使行为究竟是评价为间接正犯行为还是教唆行为本来就是难以区分的,很难想象一方面主张间接正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教唆犯的从属性。
台湾地区已故著名刑法学家林山田教授曾举过这么一个案例:A为了谋财害命而预杀害他的朋友B,可是却苦无适当的机会下手。某日,A得知性情粗暴的B与神枪手C因故交恶,A认为杀B的良机已到,乃故意从中挑拨而对B伪称:“C与你的妻子D有染,并且密谋要毒杀你。”性格暴躁的B经A的挑拨煽动,愤而持枪欲射杀C,却反而遭到身手敏捷且射击术精准的C的当场反击,将B击毙。林教授认为,在本案例中,C杀B的行为,因符合正当防卫,故属合法行为;惟C的正当防卫系A的故意挑拨所造成,并经A加以违法利用,得遂其杀B的犯意,故A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12]
倘若认为间接正犯的利用行为具有独立性,那么在A在客观上实施了所谓的利用行为,而且主观上有利用的意思的场合下,就很容易得出A成立间接正犯的结论。然而,在本案中,在客观上,A实施的仅是挑拨唆使B杀C的行为,倘若A在主观上没有利用C杀B的意思的话,无论如何,也只会将A的唆使行为作为B杀C的教唆犯处理,从而A的行为从属于B的正犯行为,即使因为C的正当防卫行为杀死了B, A依然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本案中,A有利用C杀B的意思,同时也具有教唆B杀C的故意,因此,本案中A不是涉嫌成立B杀C的教唆犯(未遂)、C杀B的间接正犯(既遂),而可能成立两个罪吗?对于同一个所谓的唆使行为,仅仅因为行为人的主观上的动机不同,而影响到行为的性质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难说这是妥当的。
利用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犯罪的,究竟是成立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在学说上争论就很大。遭受到邻居欺负的母亲唆使13岁的儿子杀死邻居,儿子同意了,手持磨得亮晃晃的菜刀深夜埋伏在邻居屋外,在邻居半夜起来小便时猛砍数刀将其砍死。不可否认,本案中,母亲唆使儿子杀死邻居的行为是利用“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的行为,若把母亲评价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此时“唆使”具有独立性。但是,由于这种结论并不妥当,于是学说上又会作为从被利用人的儿子是否有“规范障碍”、作为利用人的母亲对犯罪是否有支配,而将母亲评价为教唆犯,此时,“唆使”摇身一变,又具有了从属性。
(2)学说上虽然以“间接正犯是独立的正犯,对被利用者不具有任何从属性”为前提,但在逻辑演绎的过程中“偷梁换柱”,得出的却是从属性的结论。
在二元区分体系下,犯罪参与人被区分为正犯与共犯,共犯具有对正犯的从属性,是指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的前提,以正犯者必须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为前提,……只有被教唆人、被帮助人实施基于教唆或帮助行为,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时,才能成立教唆犯、帮助犯的未遂。[13]因此,处罚共犯必须是正犯开始着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正犯既遂,则共犯既遂;正犯未遂,则共犯未遂;在处罚预备犯的情况下,正犯与共犯都成立预备犯。
按照通说的观点,间接正犯不具有对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若果真如此,则直接行为人是否实行着手,理应不影响间接正犯是否实行着手。换言之,即使直接行为人没有实行着手,间接正犯也应成立未遂,这才是间接正犯独立性应该具有的当然含义。对于案例“母亲唆使8岁的儿子去超市盗窃,儿子却没有去超市,而是跑出去玩了”,按照间接正犯具有独立性的观点,即使儿子没有着手实施盗窃行为,母亲也应该成立盗窃罪的未遂。由于母亲实施所谓的“唆使”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法益侵害结果或危险,因此认为母亲成立未遂并不是妥当的结论。于是,理论上转而认为:因为从行为人实施所谓的利用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法益侵害结果或危险,只有把利用行为与被利用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才能决定利用行为是否成立间接正犯,才能决定间接正犯是否成立犯罪(未遂)。
然而,这种根据幕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判断幕后行为人是否着手的观点意味着,“只有幕前直接行为人着手了,幕后行为人才着手”,这其实已经不是独立性而是从属性的观点了。如林山田教授一方面“赞同利用行为说的出发点,将间接正犯的着手实行问题,依据幕后行为者的行为本身而定”,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可是若像利用行为说以幕后利用者开始或结束对于行为工具的影响时,作为判断标准,并不能圆满解决间接正犯的着手实行的判断问题,因为按照幕后利用者主观上对因果历程的想象,其客观上所从事的行为,有可能仅属于筹措必要的犯罪工具的犯罪预备阶段而已,尚未进入对于行为客体产生直接攻击行为的未遂阶段。因此,虽然判断间接正犯的着手实行的时点,应以幕后利用者本身的利用行为作为判断标准,而非取决于被利用工具的行为工具,但是被掌控支配的行为工具是否已经朝着目标前进,或者已经进展至何阶段,则属判断幕后利用者所操纵导引的犯罪因果历程是否已经对于行为客体造成直接危险时,所必须考量的事实”。[14]可是,这还是独立性说吗?难道这不正是从属性的观点吗?
不得不指出,间接正犯独立性说表面上采取的独立性说,实质上采取的却是共犯从属性说的论证方法,得出的不是独立性说而是从属性说的结论,不能说这还是独立性说。总之,凡是以被利用者开始实施具有法益侵害结果的具体危险的行为之时作为间接正犯实行着手的判断标准的,就已经说明间接正犯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具有从属性了。
(二)从属性说的正当性
1.认为间接正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符合法益保护主义要求
根据法益保护主义,违法性的本质在于法益侵害或危险,只要没有法益侵害或危险,无论行为的样态如何,也无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有多么严重,即使行为严重侵害了社会伦理秩序,也不具有违法性。即使是采取(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的立场,除了考虑行为样态上的规范违反性或伦理违反性,同样会考虑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只要没有产生法益侵害或危险,同样不会认为行为具有违法性,间接正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的见解符合法益保护主义的要求。
2.根据实质的客观说,间接正犯的“回溯性”判断方法表明间接正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
就间接正犯而言,只有所谓的利用行为,还没有被利用行为时,还不能说利用行为本身已经具有违法性,只有被利用人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时,才会判断利用行为的性质。因此,在犯罪参与中,幕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必须采取这种回溯性的思考方法才能确定。这种回溯性的判断过程本身,就表明了间接正犯对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
3.没有幕前行为人就没有间接正犯,而幕前行为人是否不法与有责并不影响间接正犯的成立,因此间接正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
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而行为是否侵害或威胁了法益,与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以及有无故意、过失没有关系。精神病人杀害他人的行为与正常的人杀害他人的行为,在侵害了他人生命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差异。[15]换言之,间接正犯“只是一种犯罪现象的描述,被利用人是否不法、是否有责对于间接正犯的成立并无重要意义,刑法所关心的仅仅在于利用人对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支配”[16],因此,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结果或危险)的行为,就是直接行为人;如果幕前行为不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那么幕前行为就具有违法性,直接行为人就是违法层面的直接正犯;至于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等消极的责任要素,则是在犯罪成立判断上,在有责性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在犯罪的结构或与被害人的关系上,间接正犯与共犯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构,都是通过幕前行为人即直接行为人间接侵害法益,从而实现自己的犯罪;从违法的层面上看,所有的间接正犯都可以称为“(直接)正犯后的正犯”。因此,从间接正犯的结构上,也可以看出,间接正犯与共犯一样,以直接行为人的存在为前提,没有直接行为人,就没有共犯;没有直接行为人,也就没有间接正犯。这意味着,间接正犯具有对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
4.最根本地,间接正犯是拟制的正犯,将“共犯”拟制为“正犯”并没有否定幕后行为人对直接实行人的从属性
如前所述,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具有“拟制”的性质,间接正犯既具有共犯的一面,又具有需要按直接正犯处理的一面。间接正犯概念的确立,从根本上不是为了否认对于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而是基于幕后行为人支配了犯罪过程,或者整个犯罪过程在其控制之下等理由,需要在违法性上的判断以及科处刑罚上,给予其直接正犯一样的处遇。因此,将“共犯”拟制为“正犯”,并不是为了否认其对宁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
总之,作为幕后行为人的间接正犯是“拟制”的正犯,对于幕前行为人即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理所当然地,共犯对间接正犯不具有从属性,而是对直接实行人具有从属性。
三、探究: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被利用者时说
间接正犯,因为根据道具说,是利用者把被利用者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而实现犯罪的情况,所以为了成立间接正犯,必须存在利用者与被利用者。换言之,间接正犯必须具有幕后行为人通过幕前行为人实现犯罪的行为结构,即必须存在幕前行为人与幕后行为人。在间接正犯的场合,存在要么以利用者的行为的开始时期作为间接正犯的着手,要么以被利用者的行为开始时期作为间接正犯的着手的问题。亦即,在刑法理论上,关于间接正犯的着手时期,存在三种学说:一是利用者时说,即把利用者(间接正犯)开始实施诱致被利用者犯罪时作为着手;二是被利用者时说,即把被利用者的行为作为标准;三是个别化说,即以有无发生具体的危险进行个别判断。[17]
1.利用者时说的缺陷
利用者时说源自主观说。在日本刑法学中,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中的行为危险说均主张采取本说。利用者时说为通说。[18]在德国刑法学中,“具体解决方案”以“对构成行为中间人的作用作为未遂开始”,罗克辛教授等主张的“修正的具体解决方案”把“事件离开间接实行人控制范围”作为未遂开始的标准即实行着手[19],虽然按照“修改的具体解决方案”,实行着手的时期晚于“具体解决方案”,但二者仍属利用者时说;我国传统学说[20]、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21]、陈兴良教授[22]等虽然理由不一,但均主张利用者时说,利用者时说也可谓我国刑法学通说。
应该承认,利用者时说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根据从属性说,共犯对正犯具有从属性;既然间接正犯也是正犯,则当然具有独立性而不是从属性,理所当然地,就不应该根据被利用者的行为判断间接正犯是否着手实行犯罪,而必须采取利用者时说。换言之,因为正犯行为就是实行行为,而间接正犯是正犯,所以间接正犯所实施的利用行为就是实行行为;既然利用行为是实行行为,那么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就只能根据利用行为即采取利用者时说进行判断。
但是,利用者时说存在很多缺陷,张明楷教授曾经总结出利用者时说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分别是第一,利用者时说不具有现实的妥当性,或者说不符合社会的现实;第二,利用者时说扩大了处罚范围;第三,认为利用行为本身就具有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性,不符合事实真相;第四,利用者时说有自相矛盾之处。”[23]
本文非常赞同张明楷教授的总结,同时对上述总结予以进一步阐述:
(1)利用者时说木具有现实的妥当性,且扩大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案例:甲得知乙准备于特定的夜晚埋伏在甲经常散步的河边将甲射杀。甲决定利用乙的行为将仇人丙杀死,便以丙的女朋友的名义给丙发了条短消息约丙来河边约会,但是丙一直没有出现,乙不得不离开。在本案中,乙为了杀甲而埋伏在河边,但由于被害人没有到达现场,以致未能着手实施杀人行为。“守候行为”属于犯罪预备而非犯罪未遂,这个结论无论是学说还是实践应该没有争议,即利用者时说也承认乙属于犯罪预备。但按照日本的利用者时说,由于甲已经实施了利用行为,因此甲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按照德国利用者时说之“具体解决方案”,甲成立未遂;按照德国利用者时说之“修正的具体解决方案”,由于“事件已经离开了甲的控制范围”,甲也成立未遂。[24]
我们发现,在本案中,乙为了杀人而持枪埋伏在河边,甲为了杀人而发了一条短信,二者都是正犯。因为被害人没有去现场,所以作为直接正犯的乙根本不可能实施“端枪瞄准”被害人,甚至“扣动扳机”之类的“实行着手”行为,可是按照利用者时说,间接正犯在发短信息的时候就已经着手“杀人”了。我们还注意到,本案中,主观上甲乙二人具有同等的恶,客观上乙的持枪埋伏行为应该比甲发短消息的行为更具有法益侵害可能性,乙的行为的违法性程度理应更重,即使不是更重至少是具有同等程度的违法性。可是,对于行为的违法性程度更重的乙反而处罚轻,即可以根据《刑法》第22条对乙“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根据《刑法》第23条对于甲“从轻、减轻”但“不能免除处罚”。由此可见,按照利用者时说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具有妥当性。在前例中,甲的行为尚未“实行着手”,只能与乙的行为一样评价为犯罪预备,但利用者时说认为甲的成立犯罪未遂,因此利用者时说不当扩大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再如,父亲在家唆使10周岁的儿子上学的时候去把同学的苹果手机偷回来,但是儿子反过来批评父亲不对的案例中,按照利用者时说,父亲也成立盗窃罪的未遂[25],但这种结论不具有妥当性,显然利用者时说扩大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2)利用者时说认为,利用行为具有足以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然而这不是事实。[26]如前例“借刀杀人”案,只有当埋伏在河边的乙,举枪向被害人瞄准之时,才具有被害人可能被射杀的危险,仅仅埋伏在河边的“守候行为”,因尚未具备足以造成法益侵害紧迫危险而属于“预备行为”,“发短消息欺骗被害人”的所谓“利用行为”更不应该是“着手”行为。否则,在甲以丙的女朋友的名义,给丙发了条短消息,约丙来河边约会,拟亲自射杀丙的案例中,甲在发短消息之时,就也应该已经“实行着手”了。在父亲唆使孩子盗窃,孩子反过来批评父亲的案例中,孩子有非常强烈的规范意识。家与学校一定有很长距离,孩子的同学是否下次开学继续携带苹果手机也不得而知,父亲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任何侵害法益的危险。非要说危险,也不是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是父亲唆使行为征表了父亲主观恶性,但是这已经是主观主义的刑法观了。
(3)关于利用者时说的自相矛盾之处,有形式的客观说与行为危险说,一方面强调实行着手是具有法益侵害具体危险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又无视所谓“利用行为”是否真的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利用者时说一般都会主张,被利用者的行为只不过是利用行为的延长。但是“既然从规范主义的观点来看,被利用者的行为是利用者的行为,而不能认为是两个人的行为,那么,从被利用者的身体动静上认定实行的着手,也就是从正犯的身体动作中认定着手。利用者时说一方面肯定被利用者的行为是利用者的利用行为的延长,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从被利用者的身体动静中认定着手,这就自相矛盾”。[27]
本文认为,从逻辑上讲,利用者时说才是间接正犯着手的当然结论。只有坚持利用者时说才是真正坚持了“间接正犯是正犯,既然是正犯,就不可能具有任何从属性”的理论前提。然而,正是这一错误的理论前提,导致了利用者时说所具有一系列问题。
2.被利用者时说的矛盾
实质的结果说认为,“当行为发生了作为未遂犯的结果的危险性,即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了具体程度(一定程度)时,才是实行着手”[28]持实质的结果说的日本刑法学家的代表有平野龙一、前田雅英、西田典之、山口厚等。就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实质的结果说一般主张被利用者时说,即被利用者实施的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或紧迫危险时,才是间接正犯的着手。
本文认为,不可否认被利用者时说结论上的妥当性。但是,被利用者时说存在三个主要矛盾:
(1)被利用者时说的结论与前提相悖。被利用者时说认为,间接正犯的利用行为是实行行为,这是立论的前提,而所谓“实行着手”就是“实行行为”的开始,因此,在逻辑上只有利用者时说才是当然的结论,但是被利用者时说却以被利用者开始实施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或紧迫危险行为作为判断“实行着手”的根据。由此可见,被利用者时说的结论与前提相悖。
(2)被利用者时说导致处罚对象与着手相分离。与利用者时说一样,被利用者时说也认为被利用行为是利用行为即正犯行为的因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29]或把利用行为与被利用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30],即把利用行为视为处罚对象。但被利用者时说却又认为被利用者开始实施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或紧迫危险行为时才是利用者即间接正犯的着手,结果导致处罚对象与着手相分离,这是自相矛盾的。[31]
(3)在所谓“正犯后的正犯”的场合,前述被利用者时说重复评价了“直接正犯”行为。在当间接正犯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当“正犯后的正犯”这种间接正犯类型被发现、被承认之后,前面两个问题更为明显。在多纳案例(Dohna-Fall),即“正犯后的正犯”的典型案例中,幕前行为人B有杀人的故意且实施了杀人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直接正犯。然而,依照前述“被利用者时说”,在评价幕后行为人甲的利用行为时,又把已经被作为“故意杀人罪”否定评价B的行为视为A的行为的因果经过或A的行为的一部分再次进行了评价。
3.个别化说的问题
个别化说其实是各种折中说的别称,其基本观点是不区分利用者与被利用者,在某些场合下以利用者开始实施利用行为时为着手,在另外一些场合采取被利用者开始实施被利用行为时为着手。个别化说因为理论表述上的简洁性而令人容易接受,但是个别化说存在如下问题:
(1)因为个别化说的立足点仍然是“间接正犯也是正犯,利用行为就是正犯行为”,所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时,仍然存在当以利用者时作为着手时期时会导致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扩大,当以被利用者时作为着手时期时会导致处罚对象与着手分离问题。
(2)单独正犯与间接正犯在行为结构上具有根本性区别。个别化说普遍存在不能对实行着手提供判断标准,在实践上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如在父亲唆使10岁的儿子盗窃但被儿子拒绝的案例中,西原春夫教授提出“在结果犯的场合,根据被利用者实施预定行动的盖然性的高低判断幕后行为人是否实行着手”[32],但是10岁的儿子实施盗窃的盖然性实难判断,况且这种盖然性的判断并不是实行着手的判断标准,而是幕后行为是否具有犯罪控制或支配性的“正犯性”的判断材料,亦即如果实施预定行为的盖然性高,则意味着幕后行为人是正犯而非教唆犯。基于规范性障碍说的个别化说认为,“在利用幼儿、精神病人或过失犯之类的被利用者的工具特征极其强烈的场合,由于行为人即利用者开始驱使被利用者实施犯罪的话,被利用者几乎不会有任何障碍地将利用者的犯罪意图付诸实现。在这种场合下,利用行为本身就具有引起构成要件的危险性,可以将其直接作为着手的认定标准”。[33]然而,如本案,10岁的小孩子是否为没有任何规范障碍的工具,也存疑问。
(3)个别化说中的区别理论,以被利用的幕前行为人是否有故意而采取不同的着手标准。“原则上应采取利用者基准说,但是例外地,在利用他人故意行为的情况下,应以被利用者时认定实行着手”。[34]“在通常情况下,利用者开始实施利用行为时为着手,但就利用有故意的间接正犯而言,被利用者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为着手。”[35]然而,只有以行为是否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作为判断着手的标准才是正确的观念,因为幕前行为人是否有故意只是幕前行为人的责任问题。正如罗克辛教授所言,“它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认为使用一种无故意的(也就是一种轻信的,也能够不负责任的)构成行为中间人会更有把握地导致这个结果,因此,由于间接实行人这个形式具有增加的危险性,未遂界限的一个更早的着手就得到正当化了”[36],如医生甲知道护士乙经常疏忽大意,遂把毒药掺入针剂放在乙的工作台上,意图利用第二天乙的过失行为将病人丙杀死的案例中,按照区别理论,甲把掺有毒药的针剂放在乙的工作台上即为着手,但这还只是故意杀人罪的预备行为。
4.本文的观点:被利用者时说
上述间接正犯实行着手学说都是以“既然间接正犯是正犯,就当然具有独立性,不存在任何从属性”为前提而展开讨论的。通说的观点显然忽视了“间接正犯”所具有的“拟制性”特征,亦即,间接正犯的行为本来是共犯的行为,只是因为间接正犯通过直接行为人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达到了与直接实现构成要件行为同等重要程度,要么直接行为人成为了犯罪的工具,要么后行为人支配了犯罪事实或犯罪过程事实上处于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规范的评价上必须将后行为人视为直接正犯处理。间接正犯的这种拟制性特征的背后,就是间接正犯对于直接构成要件实现者即直接行为人的“从属性”。但是这种“从属性”却被各种各样的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理论所掩埋了,认为既然是正犯,就不存在任何从属性。正是这样的前提,导致一系列有疑问的结论。
而只要毫不掩饰地承认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具有拟制性,幕前行为即被利用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并承认把共犯拟制为正犯进行处理,并没有否定间接正犯对于直接正犯的从属性,那么在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判断上理所当然地应采取“被利用者时说”。[37]
四、结论
总之,间接正犯与共犯都是通过直接正犯所实施的构成要件行为间接侵害法益,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构,只不过,共犯只是惹起或促进了直接正犯实施不法行为,而间接正犯则对犯罪事实处于支配性地位,因此,必须在规范的评价上将其与直接正犯同等对待。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论证、确认过程,其实就是消极地论证其不成立共犯,并将其排除出共犯的评价范围的过程,因此,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具有拟制性。随着间接正犯的理论发展,直接实现构成要件者即直接实行人的属性已不再影响“幕后行为人”的定性。由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具有拟制性,因此在二元的区分体系下,间接正犯概念本身并不否定其对于直接实行人的从属性。只要承认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拟制性,以及其对于直接正犯的从属性,那么在理论上就能够承认:在犯罪参与中,共犯对直接实行人而不对间接正犯具有从属性;间接正犯的利用行为、支配行为虽然是间接正犯的“正犯行为”,但是其着手则以被利用者即直接正犯的着手为标准判断成立未遂的时期。因此,对于文首的案例,共犯甲、乙、丙与间接正犯A都对直接正犯B具有从属性,所有的犯罪参与人均属预备犯,这就是基于反思间接正犯的拟制性而得出的结论。
注释:
[1]“正犯后的正犯”是“‘直接正犯后之间接正犯’的代名词”(参见黄常仁:《“间接正犯”与“正犯后正犯”》,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1页),“是指被利用人的行为符合所有犯罪的成立要件,以成立(直接)正犯,但幕后的利用者却仍因其优越的支配地位而成立间接正犯,参见蔡圣伟:《刑法问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73页。
[2]本案例改编自德国刑法学家格拉夫· Z.多纳设计的著名的多纳案例(Dohna-Fall),参见Graf zu Dohna, übungen im Stza&echt und Strafproze?recht,3. Aufl.,1929, Fall Nr.36.〔日〕高桥则夫:《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成文堂1988年版,第77—78页。
[3]〔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35页。
[4]所谓“严格从属性”是指只有正犯的主行为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而成立犯罪,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才方能有所从属或依附而成立共犯。
[5]〔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第三版),创文社1991年版,第154页。
[6]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第三版),创文社1991年版,第154页。〔日〕川端博:《刑法讲义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520页。
[7]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8]〔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_143页。
[9]参见克劳斯·罗克辛:《正犯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劳东燕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5卷)。
[10]参见〔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35页。
[11]参见陈兴良、周光权:《现代刑法学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12]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十版),2008年版第59页。
[13]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四版),有斐阁2008年版,第283—284页。
[14]林山田:《刑法通论》(增订十版),第51—52页。
[15]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16]蔡圣伟:《刑法问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81页。
[17]参见〔日〕西田典之:《共犯理论の展开》,成文堂2010年版,第89页。有关学说的详细情况,可阅读张明楷教授所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中相关内容,本文不在此赘述。
[18]参见〔日〕黑木忍:《实行的着手》,信山社出版株式会社1998年版,第84—85页。
[19]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_309页。
[20]参见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21]参见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249页。
[22]参见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23]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97—99页。
[24]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309页。
[25]按照“修正的具体解决方案”,父亲成立犯罪预备而非未遂。
[26]如大塚仁教授认为,“一般都能从利用者的诱致行为上看出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利用者的诱致行为开始时是实行的着手,并无特别的不合适”。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四版),有斐阁2008年版,第174页。赵秉志教授主张,“间接实行犯所实施的利用行为即足以对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造成现实的危险”,因而采取利用者时说。详细见解参见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27]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99页。
[28]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1页。
[29]参见平野龙一教授即持此种见解(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有斐阁1975年版,第319页)。
[30]德国学说将其称为“整体解决方案”。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31]参见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101页。
[32]〔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33]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7页。
[34]〔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有斐閣2008年版,第405页。
[35]〔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4版),有斐閣2008年版,第173页。
[36]〔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37]当这样理解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间接正犯与直接行为人的关系时,被利用者时说被认为具有的三个矛盾完全不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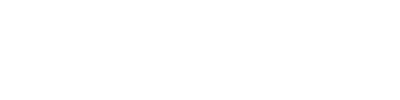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