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兵
【摘要】交通肇事罪中的“因而”,显然旨在强调交通违章行为与重大事故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缺乏救济程序的行政确认行为,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只能作为一种勘验证据材料使用;应区分交通行政管理规范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只有触犯后者的交通违章行为才可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便是无证驾驶、超速、超载、酒驾等典型交通违章行为,也应在个案中具体判断是否事故发生的原因;“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具有合理性,只是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直接加以规定,同时将推定负全责的逃逸者的刑事责任限于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
【关键字】交通肇事罪;因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果关系;肇事逃逸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中的“因而”,显然旨在强调,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以下简称“交通违章行为”),必须与重大事故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只要行为人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交通违章行为,客观上又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现象。例如,行为人驾驶未经登记、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未经年检的车辆上路,客观上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即认为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然而,《道交法》作为行政法所规定的种类繁多的禁止性规范,并非都是直接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的规范,交通违章行为未必就是具体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此外,司法实践中不乏以被告人违反了《道交法》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原则性规范为根据,直接认定其成立交通肇事罪。可以说,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上,普遍存在混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混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刑事责任认定、错当原则性规范为规则性规范予以适用的现象。[1]究其原因显然在于,无视交通肇事罪中“因而”的规定及其认定。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道交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道交法》还是《实施条例》,都未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的救济程序。这说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缺乏救济程序的行政确认行为。
可是,就是这种救济途径阙如的行政确认行为,不仅关系到当事人民事赔偿权实现的程度,而且直接关系到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及其轻重。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2条及第4条,直接根据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是负全部、主要责任,还是同等责任,确定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和加重犯。虽然《道交法》第73条肯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在有关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上成为了法院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及其轻重的重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2]坦率地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案实际上不是由法院审理裁决,而是异化为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主导断案,而有失司法公正。[3]这种现象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对此,刑法理论上毫无争议地认为,“刑事司法机关在审理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不能直接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而应根据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分析判断,避免直接将道交法责任转移为刑事责任”[4]。之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因为:(1)道路交通行政管理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存在明显区别,道交法上的责任明显不同于刑事责任;交管部门在认定当事人的责任时,并没有考虑刑事责任的根据与条件,常常只是简单地综合行为人违章的多少与情节做出责任认定。[5](2)众所周知,行政责任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安机关依据其职权作出的关于事故当事人责任划分的一种行政责任认定,即使责任认定存在错误,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而其只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一种证据。[6](3)从刑事诉讼法角度讲,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符合证据要求,不属于刑事司法机关必须采纳的证据材料。(4)交通事故认定系行政行为,着重于事先预防,一般只考虑事故双方各自有无违章行为,不重视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刑事责任的认定,在客观方面强调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交通违章行为,必须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总之,由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在事实证据、构成要件等方面的认定原则、方法、要求不同,如果将行政责任认定结论直接作为认定当事人构成犯罪的依据,则意味着,刑事案件的审理实质上演变为由公安机关主导,司法审查流于形式,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7]
综上,由于刑法目的明显不同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只能将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单方做出的、缺乏必要制约和救济程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视为一种参考性的勘验证据材料,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及其轻重的根据。
二、交通法律规范的分类
(一)交通行政管理规范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
根据交通法规是单纯指向交通行政管理的目的还是直接关系到交通运输安全,可以将交通法律规范分为交通行政管理规范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8]
《道交法》中属于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主要是第8、11、15、16、17、18、98条所规定的,关于机动车、非机动车登记,机动车相关标志、图案、报警器或标志灯具等的合法合规使用,以及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仅存在违反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交通违章行为的,由于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通常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交通肇事罪中“因而”的要求,不应成立交通肇事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警部门”)将违反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违章行为,直接作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根据,而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不过是“照收照转”。例如案1: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违反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驾驶未经登记、无牌号和行驶证的车辆在路况良好的路段行驶时,未能确保安全通行,将被害人廖某撞倒,造成廖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在肇事后逃逸。”[9]很显然,“驾驶未经登记、无牌号和行驶证的车辆”不可能是事故原因。法院之所以将其写进判决书中,是因为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了上述违反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所谓违章事实。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应当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安全规范的违章行为中,找出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原因,认定存在交通肇事罪的具体实行行为,进而肯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10]
《道交法》中属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的,主要是第13、14、19、21、22、38、42、43、44、47、48、49、51、56、61、62、70条所规定的,关于机动车行驶规则,载物、载人规则,机动车停放规则,行人通行规则以及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要求等方面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行为人存在违反交通运输安全规范的行为,也应具体分析该违章行为是否具体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否则,也会因为不符合“因而”的要求而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倘若实际车况良好,驾驶未经年检或者超过报废期限的车辆,就不能认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例如案2:被告人张某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轿车撞死横过道路的77岁被害人。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轿车行驶过程中疏于观察前方路面车辆动态,遇有情况未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且案发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11]判决在未查明被告人驾驶的未定期年检的车辆是否存在技术隐患的情况下,就将驾驶未定期年检的车辆作为事故的原因,恐有不当。
(二)保障自身安全的规范与保证他人安全的规范
《道交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要求使用安全带、戴安全头盔,显然旨在保障行为人自身的安全,而不在于保证其他交通参与人的安全。[12]在前车未开车灯,后车也未开其车灯,致使前车发生事故的案件中,要求后车行驶时应当打开车灯,显然是为了保证自身行车的安全,而不是要求其车灯在行驶中起着公共照明灯的作用,故未开车灯的后车驾驶员不应对事故的结果负责。[13]
(三)原则性规范与规则性规范
当存在具体的规则性规范时,不应适用原则性规范进行责任认定。例如,《道交法》第22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即属于原则性规范。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应当查明,是否存在违反具体规则性规范且与事故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违章行为,而不能直接适用原则性规范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例如案3:交警部门认定,“黄某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小型普通客车未保持安全车速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14]。其中所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即为直接适用原则性规范认定责任,故而不妥。
三、典型违章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
(一)无证驾驶
虽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通常不具有驾驶和控制车辆的能力,但不能由此认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就一定不具有驾驶车辆的能力,也不能认为具有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就一定具有驾驶能力(如取得驾驶证以后多年未驾驶机动车,甚至是开“后门”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易言之,是否具有驾驶技术与是否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无直接关系。[15]况且,即便行为人缺乏驾驶技术,在具体个案中,缺乏驾驶技术也未必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比如行人跨越护栏突然闯入封闭的高速公路,驾驶者刹车不及撞死行人。所以,即使存在无证驾驶的违章行为,在具体个案中也应具体分析无证驾驶是否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否则也会导致“因而”的认定错误。例如案4:被告人刘某无证驾驶面包车,与骑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的被害人薛某相撞,致薛某颅脑损伤当场死亡。被告人事后找陈某“顶包”。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无证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肇事后逃逸,致一人死亡,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16]很显然,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被害人突然横过道路,而不是被告人的无证驾驶行为。或许,无证驾驶以及为逃避法律追究找人“顶包”的事实,可以作为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根据,但不应成为法院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主要依据。法院应当查明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分析违章行为是否满足“因而”的要求,进而认定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
总之,除非能够证明事故是因行为人缺乏驾驶技能所致,否则难以肯定无证驾驶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因而”的要求。
(二)超速驾驶
禁止超速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使驾驶人能够保持清醒而集中的注意力,以便对行人或其他车辆的安全等路面情况全面观察,及时发现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化解交通险情”[17]。易言之,禁止超速驾驶,是为了防止在出现险情时来不及采取制动措施。如果行为人即使不超速,也几乎不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则难以认为超速驾驶是事故的原因。对于夜间以时速58公里行驶在限速50公里的市区道路上,撞伤突然穿越马路的行人致其死亡的案件,德国判例认为,由于即使行为人不超速,也难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则事故的原因不能归咎于超速驾驶。也就是说,即使超速驾驶,仍有适用信赖原则的余地。[18]总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存在超速驾驶的违章行为,就满足了交通肇事罪中“因而”的要求,而是必须具体查明超速驾驶是否具体案件中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案5:被告人杨某驾驶出租车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八街工会会馆楼前路段,以73.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倒推自行车横过街道的被害人顾某,顾某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超速行驶,发生重大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19]应该说,本案判决是正确的。虽然判决书没有交代事发路段的限速是多少,但从案情描述来看,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以73.5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应明显属于超速行驶。如果不超速行驶,当发现推自行车横过街道的被害人时应该来得及采取制动措施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案6:被告人牛某驾驶轿车将横过道路的被害人张某、刘某撞伤后弃车逃离现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牛某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牛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且肇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20]一审法院认定事故的原因为“超速”,二审法院则语焉不详。可以看出,超速是否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二审法院并未认真查明,而是根据《实施条例》第92条关于肇事逃逸负全责的规定,直接认定成立交通肇事罪。
案7:被告人赵某以时速77公里行驶在限速60公里的城市快速路段时,其所驾车辆轧在散放于路面的一个雨水井盖上后失控,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后与正常行驶的杨某驾驶的轿车和骑自行车正常行驶的刘某、相某、张某、薛某相撞,造成刘某、相某当场死亡,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杨某、薛某受伤。法院认为,“海淀区圆明园路主路北向南方向设有明显的限速60公里/小时交通标志牌,被告人赵某事发时行驶速度高于77公里/小时,由于赵某违章超速驾驶车辆,且未尽到注意义务,在其发现散落在路中的雨水井盖时,采取措施不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故赵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21]笔者认为,本案中除非能够通过侦查实验证明,如果不超速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否则,只能将该起事故归为意外事件,即,超速驾驶行为不能满足“因而”的要求,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法院判决显然未能查明该事实,故而存在疑问。
(三)酒后驾驶
禁止酒后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显然在于,防止因饮酒导致驾驶车辆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在碰到险情时判断和处置的能力不足。不过,“一名醉酒的驾驶员,在别人不尊重他的先行权和这个事故对于清醒的驾驶员来说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尽管他处于无驾驶能力状态之中,也仍然必须以信赖原理为根据宣告无罪”[22]。但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不加分析地将酒后违章驾驶的行为作为责任事故原因的现象。[23]
案8:被告人杨某夜晚醉酒驾驶(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93.6mg/100ml)轿车,搭载严重醉酒的被害人罗某(血液中乙醇浓度为353.37mg/100ml),在行驶过程中被害人罗某突然拉开车后门跳下车,跌出车外与路面搓擦后撞到人行道边沿当场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杨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搭载大量醉酒后可能失去行为控制能力的被害人罗某,未尽到应当预见危险性并采取必要防范措施的责任,行驶中车速过快,且在转弯时未减速,杨某的上述行为系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对事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故构成交通肇事罪。[24]应当说,即便被告人不是醉酒驾驶,对于作为成年人的被害人在车辆快速行驶过程中突然拉开车后门跳下车的举动,也难以预见和避免,故醉酒驾驶不是该起事故的原因,法院以醉酒驾驶为由认定成立交通肇事罪,明显不妥。
案9:被告人张某甲酒后驾驶正三轮摩托车载其子张某乙在行驶过程中,摩托车上装载的超出摩托车前方纵向装置的矩形方钢前端面与行人赵某相撞、摩托车装载的垂直于摩托车行进方向(即横向装置)超出摩托车货斗右端宽度的移动脚手架圆柱钢管工作位置下端与行人裴某相撞,致赵某当场死亡,裴某送医院后死亡。[25]本案中,显然酒后驾驶不是事故的原因,违章装载才是事故的真正原因,故法院认定醉酒驾驶也系事故发生的原因,明显不当。
(四)超载驾驶
禁止超载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保障汽车的安全行驶。具体而言,汽车超载会导致稳定性较差,转弯时离心力增加,如果车速较快则极易翻车,而且汽车超载时其制动效果会明显降低,尤其是在遇到下坡时加速度会增快而致机动车重心前移,容易失去控制而引发交通事故。[26]但是,在具体个案中,虽然存在超载事实,但即使不超载,事故也难以避免时,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超载是引发事故的原因进而成立交通肇事罪。[27]
案10:被告人超载驾驶(核载31400kg,实载36980kg)重型半挂货车行驶过程中,货车上的六根树桩滚落到对向车道,并与对向车道上被害人余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及被害人肖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余某当场死亡、被害人肖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小型客车上被害人赵某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超载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法院予以认可。[28]很显然,本起事故的原因应是被告人驾驶前未固定好所载货物,导致行驶中货物滚落到对向车道而引发事故。也就是说,即使不超载,事故也难以避免。故法院不应将超载驾驶认定为事故发生的原因。
(五)横穿马路
众所周知,中国人一向无视交通法规,对于交通信号灯尚且视而不见,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不注意观察来往车辆而突然横过道路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机动车撞死了人,基本上就认定机动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29]长此以往,只会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更加无视交通规则、更加有恃无恐地违章横过道路,从而酿成更多的人间悲剧,同时严重影响机动车的正常运行速度。
案11:被告人张某于晚上8时许驾驶轿车,撞倒醉酒后横过道路的被害人郑某,造成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张某负主要责任,法院予以确认。[30]本案中,醉酒的被害人疏于观察来往车辆违章横过道路,应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法院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被告人责任,可能欠妥。
案12:被告人王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骑自行车横过道路的被害人刘某相撞,造成刘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该肇事罪。[31]本案中,也不排除被害人刘某骑自行车横过道路的行为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可能性,故法院的判决也不无疑问。
四、过失的竞合及监督过失
所谓过失的竞合,是指某种犯罪结果系由两个以上的人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情形。从理论上可以将过失的竞合分为对向型过失竞合、直列型过失竞合、并列型过失竞合等不同类型。过失竞合的典型是所谓的监督过失,即由于业务或者其他社会生活上的关系,负有义务监督他人不致过失造成法益侵害的人,没有履行这种监督义务而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形。[32]就交通肇事案而言,行为人超速驾驶机动车撞死违章横过道路的行人的,可谓对向型过失竞合;前面车辆因驾驶中打手机疏于观察而撞倒前面骑摩托车的人,后面车辆因超速行驶刹车不及而从被害人身上碾过致其当场死亡的,可谓直列型过失竞合;两名司机轮流驾驶长途货车,一名司机驾驶时走神,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另一名司机未及时提醒导致追尾撞上前车的,可谓监督过失。
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应该说,这是对交通肇事案中监督过失的肯定。不过,也有学者一方面肯定这种情形属于监督过失,但同时认为,司法解释对这种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性不够妥当,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33]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之间,并非对立排斥关系,而是一种竞合关系。换言之,交通肇事罪很多时候也可谓一种重大责任事故,只不过是发生在交通道路上的责任事故。因此,对于上述人员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在道路上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应以作为特别法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定只是对交通肇事罪中监督过失的一种列举性规定,上述以外的人员,只要符合监督过失的成立条件,也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但司法实务中有人将上述规定理解为封闭性的特殊规定,认为由于车辆借用人(非所有权人)不属于上述人员,其指使他人违章驾驶的,根据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罚的原则,不能追究指使人的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34]其实,不仅借用人指使、强令违章驾驶,可以成立交通肇事罪,而且乘车人指使出租车司机超速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也能成立交通肇事罪的过失的单独正犯(而非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典型的交通肇事过失竞合的案件。
案13:被告人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右转弯时,因其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与骑摩托车的被害人王某相撞,致王某骑摩托车侧滑,与对面驶来的姚某驾驶的公交车相撞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驾驶非机动车转弯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姚某驾驶制动不合格的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被害人王某驾驶机动车没有确保安全行驶也是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法院予以确认。[35]该案属于三方过失竞合的情形。
案14:张某在为开普公司厂区改造工程施工过程中,雇佣被告人周某驾驶未经注册登记且安全性能不合格的无号牌的小型四轮翻斗车拉土。被告人周某在驾车拉土过程中横穿公路时,与被害人侯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侯某当场死亡,乘坐摩托车的被害人庄某受伤。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驾驶未经注册登记且安全性能不合格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张某雇佣被告人周某为其施工,所提供的用于施工作业的翻斗车属未经注册登记且安全性能不合格的机动车,其作为接受劳务者应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36]笔者认为,如果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雇主张某所提供的机动车的安全性能不合格,而且张某明知其所提供的机动车安全性能不合格,则张某应承担监督过失的责任,也应成立交通肇事罪。故法院的判决存在疑问。
案15: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被告人孙涛,在发生事故前将该车的一个刹车鼓有裂痕、一个刹车片磨薄、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况,告知了汽车经营者被告人丁某。被告人丁某未能及时安排被告人孙某进行维修,并示意被告人孙某继续驾驶该车进行营运。后被告人孙某在驾驶该车过程中由于制动失效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五人死亡、三人受伤的重大事故。法院认为,“上诉人孙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超载,致车辆失控,造成五人死亡,三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上诉人丁某作为陕B15660号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经营者,在明知该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安排及时进行维修,指使该车驾驶员继续上路营运,造成事故的发生,且该车司机孙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亦构成交通肇事罪。”[37]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案16:黄某与邓某约定,由邓某用自己的车辆为黄某运土,黄某按车次支付邓某费用。邓某驾驶未经年检、没有营运证、没有转向灯的不具备安全运输条件的车辆为黄某拉土过程中发生致2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法院判定,被告人邓某构成交通肇事罪;黄某作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对承揽人邓某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条件具有审查的义务,而黄某却未予以认真审查,仍然让邓某驾驶不具备安全运输条件的车辆为其完成工作,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具有过错,对承揽人邓某交通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8]本案不同于案14与案15的地方在于,该案中的车辆驾驶人邓某与黄某之间只是承揽合同关系,车辆为邓某自己所有,故无论黄某应否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因其不负监督过失责任,其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故法院判决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正确的。
案17:车主庄某未拔车钥匙,允许饮酒者被告人刘某独自在其车上休息,后刘某擅自驾车肇事致人死伤。一审法院认为车主庄某不应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该案民事赔偿部分被发回重审,法院再次审理认为,“由于机动车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主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庄某明知刘某饮了酒,还允许其独自一人留在车上并不取走车钥匙,客观上为刘某实际驾车创造了条件,庄某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注意义务,因此具有疏忽大意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9]笔者认为,无论车主庄某应否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由于被告人刘某虽然饮了酒,但仍属于具有完全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其应对自己的行为独自承担刑事责任,即庄某的行为不应构成犯罪。
案18:汽车维修店管理人员许某私自设计,并指派本店修理工朱某,在林某和谢某所有的普通客车的后桥避震横梁上加焊一根槽钢,朱某安装后告知车主林某和谢某,加焊的槽钢太低可能会碰到刹车管,需要把槽钢割成一个弧形。被告人谢某说等晚上出车回来后再处理,当即让其雇来的驾驶员江某(事故中死亡)驾驶该车出外载客。被告人林某及其雇佣的售票员林某斌明知客车满员后,仍让站外乘客继续上车,致使核载24人的普通客车超载9人。后该车在行驶中失去刹车性能而翻下21米深的下坡,造成车上人员当场死亡8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4人,1人重伤,12人轻伤,8人轻微伤及车辆毁坏的特大交通事故。法院认定,汽车维修店店主伊某以及维修店具体管理人员许某的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车主林某、谢某以及售票员林某斌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40]笔者认为,由于维修店工作人员并不对车辆驾驶负有监督过失责任,故法院将汽车维修店店主及管理人员的行为独立评价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将与违章驾驶和事故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车主与随车售票员的行为单独评价为交通肇事罪,应该说是正确的。
五、理性对待“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
《实施条例》第92条第1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就是所谓“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我国司法实务部门一如既往地遵循该规定,只要肇事后逃逸,基本上就直接认定逃逸者负全部责任。[41]
“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遭到了理论界的一致批评,核心理由是,因逃逸行为发生在事故结果之后,该规定明显有违原因不可能发生在结果之后的基本常识,即事后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42]笔者认为,“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应对其适用进行一定的限制。
首先,众所周知,立法者之所以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时,增加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是因为当时交通肇事逃逸的现象非常普遍。据称,当时司法实践中几近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选择逃逸。[4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危害性毋庸赘言。国务院之所以在2004年颁布《实施条例》时,明确增设“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也是为了遏制日趋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的势头。
其次,虽然逃逸不会成为其他犯罪进行过错推定的根据,但交通肇事逃逸具有特殊性。如所周知,发生在车流频繁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不仅发案率高,而且发生后需要迅速抢救伤者、分清责任、恢复道路畅通。一旦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伤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且事故的责任难以分清,发生事故路段的交通也无法迅速恢复。正因为此,域外国家和地区通常将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不履行报告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例如德国刑法第149条规定有擅离事故现场罪,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有违反报告义务罪与违反救护义务罪,《加拿大刑法》规定有“违反救助义务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5条第4项规定有肇事逃逸罪。[44]既然域外普遍存在将肇事后逃逸单独作为犯罪处罚的刑事立法例,我国做出对逃逸者推定负全责的规定,也就不足为怪。目前的不足在于,关于“逃逸者负全责”,不应由立法位阶较低的行政法规进行规定,而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道交法》中直接予以规定,而且应表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过错的除外。”
最后,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轻于普通过失犯罪,规定“逃逸者负全责”并承担基本犯的责任,不至于使逃逸者承受过重的刑罚。从国外刑事立法例看,交通肇事罪作为典型的业务过失犯罪,其法定刑通常重于普通过失犯罪,但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结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立案及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明显轻于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既然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及入罪门槛不及普通过失犯罪,推定逃逸者负全责,既能满足一般预防的需要,最大限度地震慑犯罪分子和减少交通肇事逃逸现象,也不至于使逃逸者承受过重的刑罚。考虑到逃逸者负全责毕竟只是一种推定,故无论事故结果多么严重,对于逃逸者应限定在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法定刑幅度内处罚。
虽然司法实践中普遍按照“逃逸者负全责”规定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但也有个别法院在查明事故原因后,实事求是地按照责任大小进行处理。
案19:被告人陈某将大货车停靠路边等人,期间被害人张某酒后驾驶小型客车追尾碰撞陈某的大货车尾部,导致被害人张某当场死亡、客车上乘客关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陈某驾车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陈某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张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驾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交法》第70条第1款、《实施条例》第92条第1款的规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陈某以其事后逃逸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在前,陈某的逃逸行为发生在后,其逃逸行为并非引发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至于陈某有无其他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如陈某是否在禁止停车路段停车、其停车是否阻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陈某的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应否对事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一审没有查明,在事实不能查明的情况下,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如果陈某有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停放车辆从而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违规行为,结合本案事实,陈某也只应负同等责任以下的事故责任。而公诉机关仅指控陈某有逃逸的违规行为。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45]笔者认为,二审法院的分析是正确的。
案20:吴某驾驶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与同向在前由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的后部发生碰撞后,致电动三轮车向左前方滑移,使得电动三轮车的前部左侧又与宗某驾驶的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半挂车的前部左侧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宗某驾车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宗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法院予以确认,判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46]本案中,虽然被告人宗某事后逃逸,但法院没有推定其负全责,而是认定其负主要责任,应该是考虑到先前吴某与王某的追尾碰撞也系事故的原因。不过,从案情描述来看,如果宗某系正常驾驶,当时来不及采取制动措施,则其碾压被害人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不应对事故结果负责,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注释】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1]参见张卫彬、叶兰君:《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56页;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期,第5页。
[2]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玉中刑一终字第202号刑事裁定书;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运中刑一终字第8号刑事裁定书;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刑二终字第0002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酒刑一终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4)潍刑一终字第207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绵刑终字第2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等等。
[3]参见张卫彬、叶兰君:《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58页。
[4]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期,第8页。另参见李朝晖:《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44页;万尚庆、常明明:《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第61页;张卫彬、叶兰君:《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58页;劳东燕:《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学》2013年第6期,第8页;谭滨、赵宁、瞿勇:《我国刑法分则中空白罪状的解释规则探讨:兼以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为例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第159页。
[5]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期,第5-6页;李朝晖:《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43-145页。
[6]参见万尚庆、常明明:《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第60页。
[7]参见张卫彬、叶兰君:《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57-158页;陈洪兵:《公共危险犯解释论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以下。
[8]参见刘艳红:《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5页。
[9]参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4)江刑初字第497号刑事判决书。类似判例,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刑终字第0002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10]参见李朝晖:《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45页。
[11]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泰刑一终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
[12]未戴安全头盔虽然不可能是导致交通相对方死伤的原因,但可能成为被害人扩大危害后果的因素,因而被害人未戴安全头盔,可能成为事故的次要原因。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玉中刑一终字第235号刑事裁定书。
[13]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1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玉中刑一终字第226号刑事裁定书。
[15]参见赖正直、朱章程:《日本刑法中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述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5期,第122页;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期,第6页。
[16]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刑二终字第88号刑事裁定书。类似判例,参见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宜中刑终字第00161号刑事裁定书;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刑二终字第0002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17]刘艳红:《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4页。
[18]1963年12月20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BGH VRS 26,203)。
[19]参见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1999)兴刑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类似判例,参见新疆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4)阿中刑终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
[20]参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2014)兵六刑终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
[21]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刑终字第3679号刑事裁定书。
[22]Claus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4.,Auflage,C.H.Beck München,2006,S 1071.
[23]参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滨中刑一终字第58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03)金堂刑初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1999)雨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刑终字第00261号刑事判决书。
[24]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宜中刑一终字第172号刑事判决书。
[25]参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刑终字第00261号刑事判决书。
[26]参见刘艳红:《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与交通过失犯的成立》,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6页。
[27]参见陈洪兵:《公共危险犯解释论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28]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刑终字第1227号刑事裁定书。
[29]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随州中刑终字第0008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刑二终字第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刑二终字第88号刑事裁定书;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新中刑一终字第104号刑事判决书,等等。
[30]参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新中刑一终字第104号刑事判决书。
[31]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刑二终字第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32]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2页。
[33]参见刘源、杨诚:《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辨析》,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8-160页。
[34]参见曾涛、张英平:《车辆借用人指使他人违章驾驶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2期,第40页。
[35]参见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宿中刑终字第0104号刑事判决书。
[36]参见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庆刑一终字第149号刑事裁定书。
[37]参见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桐中刑一终字第00011号刑事裁定书。
[38]参见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三刑终字第86号刑事裁定书。
[39]参见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03)金堂刑初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类似判处车主仅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中少刑终字第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40]参见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南刑终字第146号刑事裁定书。
[41]参见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08)虎刑初字第0365号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玉中刑一终字第202号刑事裁定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刑二终字第88号刑事裁定书,等等。
[42]参见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期,第6页;李朝晖:《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45页;吴云:《交通肇事罪认定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8期,第118页;万尚庆、常明明:《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第63页;谭滨、赵宁、瞿勇:《我国刑法分则中空白罪状的解释规则探讨:兼以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为例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第159页。
[43]参见刘艳红:《再论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2页。
[44]参见姜敏:《交通肇事逃逸罪可行性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第102页;李会彬:《“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独立性解读》,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第122页。
[45]参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5)南刑初字第1964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一终字第68号刑事裁定书。
[46]参见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亳刑终字第00354号刑事裁定书。
作者简介:陈洪兵(1970-),男,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刑法解释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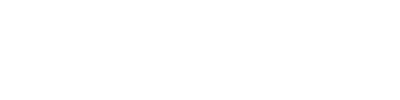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